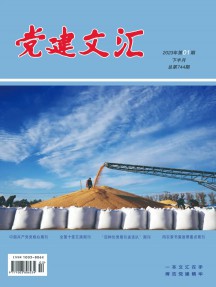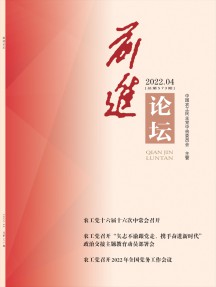政治哲學的框架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5 10:22:39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政治哲學的框架,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摘要】 目的 探討血乳酸清除率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評分Ⅱ(APACHEⅡ)對評估危重癥患者預后的價值。方法 采集入住ICU室的119例危重癥患者的APACHEⅡ評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比較不同APACHEⅡ評分段與乳酸清除率的相關性及預后評估價值。結果 (1)不同APACHEⅡ評分段與乳酸清除率相關性:r=-0.680,P
【關鍵詞】 危重癥患者;血乳酸清除率;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分Ⅱ
急性生理和慢性健康評分Ⅱ(APACHEⅡ)系統是根據急性病理生理改變及慢性基礎病變進行綜合評分,在國內外已經較多的應用于危重患者的評估中。但該評分方法較為繁瑣。本文通過對重癥監護病房(ICU)收治的危重患者6h血乳酸清除率及APACHEⅡ評分相關的觀察,探討對危重癥患者預后評估更加方便、實用的指標。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本院急診重癥監護病房(EICU)2005年3月-2009年2月資料完整的119例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68例,女51例;年齡18~79歲,平均(52.6±21.2)歲。感染性休克38例,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12例,創傷性休克19例,急性中毒25例,重癥急性胰腺炎13例,產科重癥患者12例(妊娠急性脂肪肝4例,產后大出血6例,圍生期心肌病2例);存活80例,死亡39例。
1.2 方法
(1)所有患者入住EICU后取其24h內各項生理參數和實驗室檢查結果的最差值進行APACHEⅡ評分,病房評分將患者分為4組,≤10分組(A組),11~20分組(B組),21~30分組(C組),>30分組(D組)。(2)記錄入院時和積極治療后6h的血乳酸水平,計算乳酸清除率。公式:6h乳酸清除率=(初始血乳酸水平-治療后6h血乳酸水平)/初始血乳酸水平×100%。
1.3 統計學處理
運用SPSS17.5統計分析軟件處理數據。計量資料以x±s表示。計數資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均數間兩兩比較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以P
2 結果
2.1 各組患者血乳酸清除率、病死率的比較及相關性分析
B組乳酸清除率低于A組,差異無顯著性(P
2.2 存活組與死亡組患者APACHEⅡ評分與6h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較
死亡組中APACHEⅡ評分高于存活組,而6h血乳酸清除率低于存活組,見表2。表2 存活組與死亡組的APACHEⅡ評分及血乳酸清除率的比較
3 討論
乳酸是糖酵解的代謝產物,主要產生于骨骼、肌肉、腦、紅細胞,經肝臟代謝后由腎臟排泄。重癥患者常有乳酸代謝紊亂,產生高乳酸血癥。大量研究揭示血乳酸水平與危重病的嚴重程度和預后密切相關。血乳酸越高,病情越嚴重,疾病的預后越差。由于患者肝臟、腎臟、既往藥物應用史等基礎狀態不同,受到的應激強度也不同[1,2]。因此,動態觀察血乳酸水平或乳酸清除率比單純血乳酸指標更能反應機體的實際危重程度。有研究發現血乳酸濃度在24h內恢復正常水平的膿毒癥患者幾乎100%存活,而在6h內血乳酸濃度持續升高的膿毒癥患者往往有較高的病死率。
本研究分析結果表明:隨著APACHEⅡ評分分值的增高,6h血乳酸清除率顯著下降,二者存在顯著負相關(P
APACHEⅡ評分是評價患者基礎狀態和所患疾病嚴重程度的評分系統,它不僅可用于群體ICU患者預后,而且對個體病死率的預測也有一定價值,其分值與病情嚴重程度密切相關,分值越高,病情越重,死亡風險越大。但它計算較為繁瑣,在快捷性、實用性上有一定限制。
綜上所述,聯合APACHEⅡ評分及6h血乳酸清除率可以更有效、快捷的評估危重患者的預后,亦可能盡量避免了其他因素對血乳酸水平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Chen HY.The clinic practice of blood lactates acid and gas in acute critical illness from ICU.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2007,6(7):91-92.
2 Jons AE,Shapiro NI,Trzeciak S,et al.Lactate clearance vscentral venous oxygen saturation as goals of early sepsis therapy: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AMA,2010,303(8):739-746.
3 李潤銘,陳瓊駒,曾隆桂.早期血乳酸清除率在評估外科休克預后中的臨床意義.海南醫學,2011,22(15):17-19.
4 周成杰,陳國忠,安敏飛,等.感染性休克動脈血乳酸水平及乳酸清除率與APACHEⅡ評分相關性分析.浙江實用醫學,2008,13(6):410-411.
5 王亞東,黃曉英,韓旭東.血乳酸清除率與急性生理及慢性健康評分對重癥患者預后評估的比較.交通醫學,2011,25(2):179-182.
篇2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一書出版于1983年。該書構思的框架很有意思。錢先生將學術視為嵌入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知識系統。他認為:“文化異,斯學術亦異。”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中國重和合會通,西方重分別獨立”的不同學術品格。在他看來,“五四”運動所導致的主要學術后果就是“專家之學”的流行。在這一風氣的影響下,中國的古代典籍漸漸淪為以西學的理論框架加以分析整理的經驗材料,其效用無非是證明西方學術思想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于是乎,哲學界遂有“不先讀康德哲學,無可明朱子之思想”的說法。而在史學界,則流行“以西史作準繩,以國史作注腳”的風氣。這里隱含著一種“西方獨正”的學術觀與歷史觀。
錢穆先生對此加以諷刺說,生在康德之前的朱子,已經預知后世西方會有一位叫康德的出世,所以事先就把自己的哲學弄得與康德相似,這真“可謂極人類之聰明至矣!”其對學術界那種盲目崇新崇洋風氣的針砭,可以說是入木三分。
為了矯正現代中國人獨尊西學、盲目推崇專家的流俗學風,錢先生從中西學術之異出發,將現代學術的分科分為12目,包括中國的宗教、哲學、政治學、社會學乃至音樂、藝術等等,一一還諸傳統,通過對兩者的參互比較,衡論短長,使古今中西的學術建立起一種有意義的聯系,從而證明“中西新舊有其異,亦有其同,仍可會通求之”。
論本書的寫作框架,《現代中國學術論衡》這本書無疑有其長處。
對“五四”以來全盤的整體的反傳統主義的知識惡果,對西方學術淺嘗輒止生吞活剝的流弊,以及盲目推崇專家之學的荒誕,本書有著相當廣泛的揭示。
比如對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一語,如錢著指出的,這其實是說古代君主尊禮士人,對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賜其自盡。時至今天,卻還不乏學術界中人用“官官相護”來加以曲解。再如古代儒學原本有著“為儒即為政”的傳統,但在近代中國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中,自居為儒者的人早已經視政治為畏途,使往昔“治國平天下”的儒學,根本喪失了政治的維度。但反過來,如果我們以為在行為主義籠罩下的美國政治學系讀過博士,研究過投票行為的人,作為政治家即可勝任愉快,那恐怕也是十分可疑的。
錢先生寫作此書之際已經年屆耄耋,無論從本書框架設計的要求,還是對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發展的了解而言,顯然都已經力有未逮,所以就全書具體論述的細部而言,不免瑕瑜互見,既閃現作者的靈光洞見,間或也雜有荒誕不經之說,如“通神術”等等。
本書在比較闡釋的過程中,有時不免將學術研究的對象與學術理論本身加以混淆。對于學術的中西新舊之間,本書也往往缺乏細致的辨析。比如錢先生推崇中國傳統的“通儒之學”,對現代的學科劃分多有批評,視之為西方學術的不足。實際上,西方古典時代一樣推崇“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與其說這是中西學術的區別,不如說是由于現代性的登場給中西古典知識傳統帶來的共同挑戰。他關于中西之辨的許多論述,其實不過是古今之別。所以,我們最好將此書視為一部學術散論或隨筆,而非專門著作。
這樣說并不是否認中西學術之間存在的差異。華夏文化的終極之物曰“道”,而西方文化的終極之物則是“邏各斯”,借用錢穆先生以前曾指出過的,中國人往往不大相信在現實世界之外有一個本體界的存在,這一中西文化的核心差異,或許才是辨析中西古今的根本所在。
現行社會科學的學科劃分,是在19世紀實證主義的主導下,以自然科學為理想范式重新加以構造的結果。由于這一學術分科過于專門化,導致人類知識之源的日益枯竭,甚至可以說已經到了“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的地步。
經過幾十年來對惟科學主義的不斷批判和反思,這一建制即使在西方也受到強烈的批判質疑。如美國保守派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當年就要求回到古典哲學去。哈耶克則成立朝圣山協會主張打破學科壁壘,以實現知識的廣泛交流。晚近華勒斯坦則認為,社會科學正在面臨“已知世界的終結”。
篇3
三種理解模式的爭論
客觀地說,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是起點,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概念史的研究模式是它的發展及反思的結果,并共存于當代政治哲學之中。一般而言,人們對基本概念的興趣往往來自于個人境遇、實踐經驗或制度理想,而非這個概念的理解史。這決定了人們需要借助理性及政治理性的思維方法來“理解”基本概念。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應運而生,它通過設置和修改某些假設、增加一定的概念設定、采取特定的推論演繹、借助格式化的理論圖式等方法塑造政治概念。當理性重建遭遇歷史時,“歷史重建者”就粉墨登場了。正如洛夫喬伊所言,大思想家和經典文本中對基本概念的闡釋不一定具有社會代表性,它們與常用的政治和社會用語之間很可能缺乏鉤稽。在這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研究的出現就再自然不過的了。只不過前者更加偏重古典政治哲學的傳統,主張放棄當代政治哲學,反對當代政治哲學對“哲學技術”和“現代宇宙觀”的迷戀,進而回到樸素的古典時代;而后者則試圖從歷時性和共時性角度考察政治概念,既關注概念的自主的歷史演進及其歷史語義的嬗變,又注重這一過程中不同階段概念涵義與其“大環境”(社會背景、語言形態)和“小環境”(文本的語境、作者的意圖、作者的行為等)之間的因果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理性重建還是歷史重建,從它們的思維方法看,政治理論研究模式是“化約主義”的,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則是“復雜主義”的。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強調對統一的政治觀點的論證,往往具有明顯的學理范疇和基本框架,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在相應的論證框架內才具有意義,這種融入和應用體現為對歷史理解的化約處理。如約翰•羅爾斯提出:“政治觀點是關于政治正義和公共善以及哪種制度和政策更好地促進政治正義和公共善的觀點。”[8](P.5)為此,“思考關于正義這樣一種政治觀念:它試圖對這些價值做出合理的、系統的和連貫的說明,試圖弄清楚,這些價值如何被組織起來以便應用于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政治哲學的大部分著作(即使它們歷史悠久)都屬于一般性的背景文化的一部分。”與此相應,政治理論研究模式的學理范疇和基本框架大都是在政治人性的基礎上,從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出發,逐漸形成政治平等、政治自由、自由民主等政治生活的規范標準,并建構以政治公正(或正義)為鵠的的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的協調關系,由此通向更加文明的政治生活狀態[。與此不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和概念史論認為歷史理解是復雜的,而將復雜性因素化約或者進行簡單化處理,并不能真正建立一致的概念解釋的邏輯體系,概念框架不同于政治學說、政治理論及其背后的政治理性框架。他們主張歷史理解成為一種概念解釋的歷史主義意識,要用歷史的方法而不是哲學的方法來研究思想史。由此才催生了復雜主義,即從基本概念歷史理解的歷史特性出發,展示它的具體性、過去性、變動性、復雜性和多樣性。這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重視任何歷史理解都是發生在具體時間、具體地點和具體氛圍中的,盡量按照過去的樣子來理解過去,不能在不斷變動的時間之上建構絕對的一致性,應該承認歷史理解受到史料的制約而具備未知的復雜性,不能用固定的、單一的、整齊的模式對待歷史。就概念分析的相關度而言,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與概念分析的關系較為薄弱,而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和概念史研究模式都較為重視政治概念的分析。
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有兩個基本要件:概念分析與歷史分析。盡管歷史主義政治哲學十分注重歷史分析,但是它對于概念分析的態度卻不太明確。這并不是說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沒有政治概念的分析,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的理論旨趣較為宏大。其核心“是古代與現代之間永無休止的斗爭”。而施特勞斯更明確指出:“‘政治哲學’這一措辭中,‘政治的’這個形容詞與其說指明一種主題,不如說指明一種處理的方式;從這一觀點出發……‘政治哲學’的首要涵義不是指以哲學的方式來處理政治,而是指以政治的或大眾的方式來處理哲學,或者說是指對哲學的政治指引。”[就此而言,政治理論和概念史的研究模式都更為重視概念分析。政治理論的概念分析致力于發現某種受到普遍認可的概念意涵,反對存在本質上是爭議性的政治概念。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正是對政治概念存在最佳解釋的有力論證,它試圖通過引入一項邏輯大前提來從另一個幾乎無限復雜的現實中抽象出內涵的精神構造,并在剝離概念的價值負載同時強調概念僅僅是用來分析的工具。同時,他們認為對抗和分歧對把握概念的本質是重要的,但并不意味著有什么“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對概念史研究模式而言,概念分析更是其核心。它的一切研究都是圍繞概念展開的,是純粹的概念分析。即便是近年來出現了其與社會史、政治史合流并逐步關注現實政治的傾向,它的出發點也是概念分析。概念史研究模式的概念分析認為,“概念,就像個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歷史,并且鐫刻著無法磨滅的歲月風霜”。其意在使“人們遠離那種靜態的、非歷史的‘概念分析’事業,而走向一種更為動態的、歷史主義的、強調‘概念變遷’和‘概念建構’的‘概念史’。”[由此可見,因為政治理論和在歷史分析上的態度不同,所以它們二者的概念分析并不是一致的。就研究模式的邏輯而言,三種研究模式也各有千秋。其一,政治理論研究模式中,研究者一般以經典文本對概念的界定為題材,分析它們的內涵以及相互之間的傳承、發展和影響。他們一般認為不同的歷史理解都是針對某一政治概念的若干相同基本問題的思考和解答,而集中最多思考和解答的政治概念就是基本政治概念,包括自由、平等、民主、正義、共和、權力等等。這些基本政治概念的根本含義是不變的,只是在定義的形成和傳播過程中表現為不同維度、層面和領域的差異。因此,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存在確定的邏輯或體系。其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與政治理論研究模式在歷史理解的結論方面恰好相反,認為探索“政治現象的本質以及最好的或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須“面對過去思想的正確性”[。它繼承了歷史主義的“歷史意識”,但并不同意歷史主義的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歷史主義政治哲學認為歷史理解存在“顯白”和“隱喻”的表達方式,這使得政治知識和政治意見同時存在歷史理解之中,它的任務就是從政治意見之中遴選出政治知識。繼之,有關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政治知識也有“獨立的”和“傳承的”之分,而歷史主義政治哲學旨在探究前者的研究模式。其三,概念史研究模式強調“概念史”真正體現了政治世界(即政治生活及其歷史發展)的概念特性,提示人們應保持對政治世界的概念爭論及其后果的敏感,它希圖說明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普遍境況。作為人文科學的新分支,“它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特定社會語境中的語言運用,探討概念的歷史語義”。“概念史試圖用自己的方法彰顯其理論假設,即歷史見之于一些基本概念;它分析歷史經驗和理論嬗變的語言表述。不同概念的起源及其含義嬗變,是我們今天認識文化、語言和概念的決定性因素。”其包括了詞語(詞源、詞義)史、概念(概念要義、概念表述)史、范疇(概念場域、概念情境)史、實現(概念運用)史等主要內容。以外,三種研究模式的時間觀亦有不同。政治理論承認政治概念歷史的理解存在“時間距離”問題。對于這種“時間距離”,政治理論研究模式采取以今涵古的態度,認為概念史的演進就是概念邊界不斷擴大的過程,“時間距離”是在這種概念意義的包涵與擴張中被克服的。而在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的視野中,時間距離是存在的,是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但克服時間距離并非獲得歷史理解的惟一途徑,我們應該承認時間距離的客觀性,從不同階段的歷史理解中理解政治概念的整體意義。因而,歷史理解的絕對條件意味著歷史語義在理解政治概念所有條件中居于首要地位。與它們不同,概念史研究模式將時間距離作為研究的目的、意義和惟一可能存在的領域,以此反對“教義神話”、“連續性神話”、“預期神話”和“狹隘主義神話”。這一模式認為,概念史是“歷史的歷史”。由“時間距離”帶來的理解困難并非絕對的,只要真正理解歷史性質的要求,借助那些基本概念存在的時代語境、實踐環境和意識形態(或話語)背景,謹慎而持續地加以探討,就可能描繪出一幅符合基本概念歷史理解的畫卷。換言之,能夠克服時間距離的不可理解性,從而在政治概念的歷史理解與現實解釋之間建立起一些有益的聯系。
三種理解模式的啟示
對于理解公正的概念史而言,上述三種模式既有關聯,又有不同。它們提出的觀點為我們科學地理解公正概念史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提供了原則和方法。第一,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首先要具有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是指在理解公正的概念史時應將其作為一種意義的“出現”的歷史。具體而言,就是要注意公正的歷史含義及其側重的變化,以認識這一現象為目的,力求重現公正的各種基本意涵。真正的歷史意識反對片面的、孤立的“自我認識下的歷史”和“意識的歷史自我認識”,而主張將二者有機統一起來。一方面,不能離開自由、平等、正義、公正、共和、權力等現代政治術語,離開它們就無法真正回到歷史文本中去思考相應的概念表述和研究題材;另一方面,應該謹慎使用較新的、當前的概念解釋,特別警惕將今人的觀點強加給古人,為了建構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系統性、融貫性、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做出以今譬故、以新取舊的舉動。之所以說概念的歷史是作為一種意義的“出現”的歷史,是因為這一思維將“自我意識的‘近’路和意識的歷史的‘遠’路重合在一起”[15](P.17),就是說“在理性方面,哲學家假設理性闡明了歷史,因為理性屬于要求、任務、義務、調節概念的范疇,因為一項任務只有在歷史中才能實現;在歷史方面,哲學家假設歷史通過某種價值的出現和提高獲得了純屬人的資格,哲學家能再現價值和把價值理解為意識的發展”[15](P.18)。這種雙重保證和證明體現了歷史意識在政治概念歷史理解中的重要性,它是理性的概念分析和歷史的概念理解的“縫合線”。歷史意識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它能夠通過描繪具體的歷史對象、再現歷史主體的說話方式和語言所指、梳理術語符號的多樣性以及回歸文本當時的詞典(或借助工具書、大眾媒介)等具體途徑和方法加以體現。即便是學術話語或經典文本中的概念分析,研究者也可以借助多種文本的比較和梳理等方式有益于從而形成較為準確的歷史理解,減少主觀臆斷,謹慎避免印證式解釋。第二,理解公正的概念史必須認真對待時間距離問題。按照科澤勒克的觀點:“所有的概念都包含了一種時間上的聯系結構。根據有多少此前存在的體驗被融入其中,根據有多少創新型的期待內容被納入其中,每一個概念都有著不同的、歷時性的價值。”[16](P.21)存在是有時間性的,亦是有限的。這意味著,“時間總是表現為過去、現在和將來,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種時間性的距離,這種距離由于歷時久遠而成為我們讀解古典遺傳物及古典文本的障礙,它妨礙我們對它們的理解。”[17](P.129)公正作為基本概念無法在跨越時代的觀念或問題而獨善其身。三種研究模式都承認時間距離的存在,只是在如何對待和處理時間距離的問題上有所不同。不過,不論它們是主張現實超越歷史、古典代替現代還是實現概念史的“串并結構”,它們的任務都在于“克服”時間距離。但是,“時間距離”真的需要克服嗎?對公正的歷史理解不是“死”的素材而是鮮活的創造。在概念的轉換中,歷史理解既在索取意義,又在創設意義。由此可見,歷史理解創造的知識是理解公正概念史的必要條件和真正動力,在這里,時間不再是一種由于其分開和遠離而必須被溝通的鴻溝,并不是某種必須被克服的東西,而是理解的一種積極的創造性的可能性。只有從某種歷史距離出發,才可能達到客觀地認識[18](PP.420~421)。總之,時間距離不要被克服,而應被展示,“展示”時間距離中的歷史理解自然就能夠體現概念演進的邏輯,為概念的解釋框架提供“歷史前見”的基本內容。第三,理解公正的概念史需要審慎處理概念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概念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對公正而言,在術語層面它可以與正義、公平、平等、公義、公道等術語相互替換,而其符號形式更是難以枚舉。在政治理論利用統一的符號形式將概念分析的歷史與實踐建構成一個有目的性的解釋框架,這樣就是為什么正義與公正可以不加區分地被使用且justice成為公正概念的普遍符號的原因。歷史主義政治哲學發現了“符號”的歷史多樣性,并主張最原初的語言符號反映出最直接和準確的概念意義,而復合與變形的語言符號則不可避免地具有“隱喻”的性質,因而需要甄別。概念史研究模式則力圖從語言學、認識論、符號理論等學理層面上區分“符號”和“概念”。顯然,縱然不同研究模式的處理方式不同,但理解公正概念史就必須注重“概念”、“語言符號”及“意義”的相互關系。擇要述之:“一個‘概念’是一個已經‘吸融其被使用時的全部意義語境’的‘詞語’。‘詞語’因而具有‘多種潛在的意義’。而‘概念’則內在地聚合了‘大量的意義’,并且‘與語詞相比,概念總是隱晦而多歧義的’。”[4](P.78)但意義一旦與概念相結合,就從可能的觀念轉變為一種事物的品質。對于作為確定意義的概念而言,語言符號是其標準化存在形式。簡而言之,語言符號具有形式的單純性,卻是復雜的意義合成物;而概念則與之相反,它往往表現出復雜的形式性,卻具有單一的意義指向。例如,“分配正義”概念就是符號相同而具有不同概念意涵的術語,“開始于亞里士多德、消失于十八世紀后期的那個概念,和由約翰•羅爾斯根據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一些直覺而提出的概念存在很大不同”[19](P.168);而“正義就是給予每個人應該得到的東西”則出現在正義、公道、國家、公權、均衡、平均、公平等很多術語中。顯然,處理好“概念—語言符號”之間此種“復雜—合成”的意義關系是進行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方法論基礎,以符號的一致性證明概念意義的獨斷性,或者以概念意義的復雜性否定語言符號的確定性都是值得商榷的。在這里,符號選擇與概念意義的建構應該具有一致性。第四,理解公正的概念史不能忽視歷史理解的所處的語境。語境主義對政治概念歷史理解的積極意義在于為抽象枯燥的概念的歷史語言理解(例如概念與語言符號)提供了具體真實的理解網絡,從而為發現或重建一套完整的概念語匯、意義結構及與之配套的語詞符號的概念分析結構提供了較為可靠的依據。語境主義認為:“歷史都以高深莫測的方式,融合了經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經驗的厚重語境與對這一語境的含義極為重要且常常高度創造性的探索活動,它既力圖理解那種語境,又力圖促進或阻撓其中的某些特定目的。”[20]因此,語境主義方法的“注意力不應放在個別作者身上,而是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們那時代的話語之上”[21](P.118)。語境主義充分展現出歷史意識、時間距離感與概念意義的復雜性,是“普遍主義”的天敵。正如斯金納質疑“永恒正義”時所言:“不僅在于每一個思想家都是以他自身的方式來回答關于正義的問題,還因為表述這一問題時所使用的詞語在他們的不同的理論中是以如此相去甚遠的方式體現出來的,認為可以挑出任何穩定的概念來。不過是明顯的混亂。簡而言之,錯誤在于假定存在著以某一組問題,是不同的思想家都會想自己提出來的。”[21](P.86)不過,劍橋學派的語境主義并非無懈可擊,它對文本語境的強調時常會被詬病為“相對主義”。
篇4
[關鍵詞] 羅爾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爾; 正義理論; 分析哲學; 政治哲學; 當代經濟學
張國清: 羅爾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一、 引言
每個偉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學術出身和學術經歷。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學或受教育過程,他遇到的一些具體的人和事,他個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參與或經歷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學發現或科技進步、民族分裂或獨立戰爭、種族或階級斗爭、社會變革和政治革命、社會基本制度的變化和更替、國內戰爭、國際戰爭,包括在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取得的具體進展,所有這一切造就了一個思想家的具體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為一個具體時所當然的結果。我們研究和了解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就需要具體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諸多具體因素。但是,我們不能單純依賴哲學家本人說出或公開的東西,還需要研究他沒有說出或可能故意隱藏的東西。在當代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著一些沒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隱秘事物,筆者稱之為“羅爾斯的秘密”或“羅爾斯秘密”。
羅爾斯秘密的具體表現是,由于特殊的社會和學術原因,羅爾斯有意隱藏了自己的學術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東方神秘主義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國古典哲學的黑格爾因素以及解決基本政治哲學問題的當代經濟學路徑。在以功利主義為主要攻擊目標的幌子下,這些隱藏加上他一再明確表示的分析哲學的求學和研究經歷,誤導世人在分析哲學語境下來解讀他的政治哲學。像“無知之幕”、“原初狀態”、“重疊共識”、“正義原則”甚至晚年的“萬民法”等眾多概念或術語,研究者只是從單純的英美分析哲學傳統中給予解讀,忽視了它們的非分析哲學的思想來源。由于國內的羅爾斯研究者沒有注意到羅爾斯秘密,他們便對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尤其是他的兩個正義原則做出了錯誤的解讀。由于兩個正義原則在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核心地位,這種誤解所產生的學術和社會后果都是嚴重的。
自大衛?休謨以來,事實與價值的關系一直困擾著哲學家。盡管世人一般認為探索客觀真理和追求社會正義是高度一致的,但要從哲學上論證這種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紀初,邏輯實證主義的一大貢獻在于明確表示,事實是事實,價值是價值,事實與價值分別屬于兩個各自相對獨立的領域,不存在那種所謂的一致性。像艾耶爾認為的那樣,價值斷定不是科學的,而是“情感的”,“價值陳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達”[1]116。有關真理問題的探索屬于事實領域,有關正義問題的追求則屬于價值領域。后來分析哲學的發展似乎預示著屬于價值領域的政治哲學的死亡。
正當人們對政治哲學的未來感到悲觀之際,羅爾斯在分析哲學傳統中發展出了一套精細的正義理論,1971年面世的《正義論》震動了整個西方政治哲學界。羅爾斯試圖模糊分析哲學家在事實和價值之間的區分,把公平正義作為一項可靠的分析哲學工作建構起來。比如他在此書第一節里的一段話似乎要把事實和價值的關系進行全新解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實是思想體系的首要美德。一種理論如果是不真實的,那么無論它多么高雅,多么簡單扼要,也必然會遭到人們的拒絕或修正;同樣,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義的,那么無論它們多么有效,多么有條不紊,也必然會為人們所改革或廢除。”[2]3 通過仔細解讀和考察,我們發現,羅爾斯政治哲學不僅印證了黑格爾關于哲學是時代的精華之論斷,而且揭示了黑格爾關于晚近的哲學總是更加成熟的論斷。隨著羅爾斯在哈佛的兩大授課筆記《道德哲學史講義》(2000)和《政治哲學史講義》(2007)的陸續出版,羅爾斯與傳統哲學的關系部分得到了呈現。“雖然《道德哲學史講義》只是一部羅爾斯在哈佛大學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講座用的講義,但是,透過《道德哲學史講義》,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羅爾斯哲學和歷史上一些重要哲學流派的淵源關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羅爾斯作為一名哈佛大學教授的實際工作和實際身份。羅爾斯不僅是一位政治哲學家和法哲學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學家和道德哲學史學家。”[3]1《政治哲學史講義》也呈現了那種關系,羅爾斯與歷史上一些重要哲學家的思想淵源是清晰的。問題是,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究竟屬于分析哲學還是屬于歐洲大陸哲學?或者說,羅爾斯和政治哲學傳統究竟是什么關系?
除了梳理已為學界熟知的思想來源外,本文將探討“羅爾斯的秘密”,重點考察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德國古典哲學因素,為解讀羅爾斯正義理論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 羅爾斯和分析哲學:馬爾柯姆、伯林與哈特
羅爾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學家,其正義理論經由分析哲學四大重鎮(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修造而終于成型。理查德?羅蒂把羅爾斯視為分析哲學的代表:“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的區分是極其粗線條的,但它的確為區分哲學教授提供了一條捷徑。要想了解一位哲學教授究竟喜好大陸哲學還是分析哲學,只要看他書架上擺放的書就知道了。如果他的書架上都是黑格爾和海德格爾原著或者研究他們的書籍,而沒有擺上戴維森或羅爾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稱作喜好大陸哲學的教授。”[4]120羅蒂以及羅爾斯的老師、哈佛同事和同時代哲學家對于羅爾斯的分析哲學家身份幾乎已經達成共識。
羅爾斯的哲學啟蒙老師、普林斯頓大學的馬爾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維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識哲學和語言哲學領域頗有建樹,主要致力于把維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國發揚光大。他對羅爾斯的治學態度和學業方向選擇都有很大影響。馬爾柯姆向羅爾斯開設了政治哲學入門課程,這是羅爾斯在大學本科階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學訓練,以至于羅爾斯傳記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說,羅爾斯幾乎是靠自學成才的[5]2225。得益于馬爾柯姆的指導,羅爾斯選修政治哲學并以之為一生事業。
1952―1953年,羅爾斯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成為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牛津的博士后經歷使羅爾斯在學業上突飛猛進。在那里,他是基督教會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貴賓桌成員,法哲學家哈特成為他的導師。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學講座,參加以賽亞?伯林和斯圖亞特?漢普謝爾的哲學研討班,他還參加了在吉爾伯特?賴爾住所定期舉行的哲學研究小組。青年羅爾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學論文《兩種規則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對“慣例”(practice)和“行動”(action)做了區分,讓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學名篇《兩種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學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顯帶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跡,給人留下試圖把兩人思想綜合起來的印象。
羅爾斯在牛津時的這些哲學家秉承羅素、維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學傳統,注重語言分析和邏輯演繹。羅爾斯不僅繼承分析哲學的研究方法,而且繼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主題,他運用的論證方法是分析哲學常用的邏輯方法。羅爾斯試圖回答伯林的多元價值論難題。伯林認為價值多元論難題是人類必須面對的困境,而羅爾斯設計正義原則的詞典式排序,在一個公共理性框架之內,通過基本正義制度設置,盡量消除各種價值和生活方式之間的沖突,完成對兩種自由的保護,實現價值的完備性。羅爾斯一生追求構建一個可以實現的公平正義的烏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羅爾斯對待語詞的態度并非分析哲學家應持有的態度。羅爾斯對正義觀和正義概念進行了區分,提出了自己的正義觀,即作為公平的正義觀;除了有限的語詞界定外,在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中,并無太多對語詞分析的關注。羅爾斯對概念所處的語義環境亦并不十分關注,相比之下,他更關注概念在制度設計中的重要作用。羅爾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學的長處,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樣背離了分析哲學,把正義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基本結構的設計問題,當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價值領域的事物,像公平、正義、愛、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爾認為的那樣,只是人的主觀情感的表達,而具有其客觀實在性和客觀結構。羅爾斯想把“社會基本結構”客觀地揭示出來。因此,正如《兩種規則概念》中已經顯露出來的那樣,分析哲學對羅爾斯來說只具有方法論意義。
三、 羅爾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爾和斯退士
由于當時的特殊社會原因或學術原因,一些思想家會給自己的思想改頭換面,有意隱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當時不討人喜歡的某些因素。羅爾斯在建構正義理論時,是否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完全受到分析哲學啟發,來源于分析哲學,還是有意隱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歡迎的非分析因素,卻披上分析哲學的外衣?下面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在19世紀以來的英美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傳統中,一直有一個黑格爾傳統,這在古希臘哲學研究者和《柏拉圖全集》英文譯者喬維特(B.Jowett)那里有明確的起點。喬維特的學生托馬斯?希爾?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當時著名的黑格爾主義者,他對積極自由和公共產品的討論,是古典自由主義的重要轉折。格林后來成為著名黑格爾研究者鮑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師,鮑桑葵的黑格爾國家學說對20世紀英美國家學說有著深刻影響。羅爾斯的正義理論也和這個傳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格林幾乎與馬克思處于同一個時代,是英國19世紀后期最著名的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義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權利理論在英國思想史乃至整個歐洲歷史上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進入牛津大學貝利奧學院學習,師從喬維特,畢業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經擔任懷特講座道德哲學教授。格林所處的時代,勞工階級崛起,成為日益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條件和生存狀態,融入現代產業制度之中,分享現代化帶來的成果。當時英國的整個社會意識也逐漸認同或支持勞工階級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義,提出了“公共產品”和“積極自由”等概念。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格林的影響下,自由主義在英美政治哲學占據主導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義學說為英國公共政策從自由放任轉向國家干預奠定了理論基礎。
作為格林的弟子,鮑桑葵進一步發展了國家干預理論,提出了“國家至上”理論。他說:“國家的公共意志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必然是獨一無二的。”[6]1314他在這種理論中明確加進了黑格爾因素,被稱為新黑格爾主義。鮑桑葵談到了“窮人”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格林和馬克思共同關注的問題,更是后來羅爾斯關注的問題,只是羅爾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窮人”概念。“國家是最后的和絕對的調節力量,因而對每一個個人來說必然是獨一無二的。”[6]13于是,他關于國家應當在現代社會生活中扮演積極角色的主張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爾政治哲學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的聯系,有一種說法甚至將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歸結于黑格爾思想。黑格爾贊揚戰爭調和了市民社會因人們需求不滿足導致的沖突,國家之間的沖突是國家自我完善的途徑。在黑格爾那里,戰爭具有倫理學意義,它對于防止民族墮落、促進民族發展有正面作用。“戰爭是嚴肅對待塵世財產和事物的虛無性的一種狀態……戰爭還具有更崇高的意義……持續的甚或永久的和平會使民族墮落。”[7]341由于黑格爾明確鼓吹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真實爆發,人類受盡苦難,黑格爾成為眾矢之的。從此以后,黑格爾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學圈。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學學術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學家閱讀康德,接受康德的影響,卻閉口不提黑格爾。同為牛津學者,像查爾斯?泰勒那樣從黑格爾出發來解讀現代性問題的,畢竟是鳳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學傳統中,既有英美分析的傳統,也有德國古典哲學的傳統,只是德國古典哲學傳統的黑格爾因素被刻意掩蓋了起來。這一點在羅爾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體現。羅爾斯對待黑格爾的態度既有學術的原因,也有個人的原因。羅爾斯的個人經歷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創傷,使他在內心對黑格爾學說充滿著排斥,他在意識層面堅決拒斥黑格爾哲學。相比之下,他更偏愛康德。他在哈佛講授的“道德哲學史”課程幾乎以康德道德哲學研究為主題。正義理論以他對康德尊重人的觀念的解讀為基礎,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從《正義論》“正當先于善”的觀念以及公平正義的康德式解讀,到康德(以及后來的政治)建構主義和“道德理論獨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義》的道德人格觀、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區分,最后到《萬民法》拒斥世界國家(a world state)和“實際烏托邦”(realistic utopia)觀念,羅爾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跡。康德認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動。一切事物都須經過理性的裁判。根據羅爾斯的正義觀,人們在原初狀態下做出理性選擇,為免于受到侵害,人們必然服從自由平等的理性主體一致同意的原則。于是,原初狀態可以被看作是在經驗理論的框架內對康德自律和絕對命令觀念的程序性解釋。
康德強調人的自主理性,黑格爾則重視制度的優先性。在這一層面上,羅爾斯卻是接近于黑格爾而遠離康德。追隨于黑格爾之后,羅爾斯將社會基本結構視為正義的首要主題。羅爾斯特別提到,公平正義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這一政治觀念尤其適用于現代民主國家的“基本結構”。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它們在社會合作中融合成一個整體[9]389。理性制度建構是羅爾斯關注的重點,他關注的不是人們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會基本結構中實現公平的正義。由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是一部有關人類基本制度結構的設計性著作,因此,雖然羅爾斯更加欣賞康德的哲學主張,但他和黑格爾實際上有更多共同的學術偏好。
因此,羅爾斯一直掩蓋他與黑格爾的聯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只好掩蓋其同另一個未曾公開露臉的人物的關系,他就是斯退士。羅爾斯從本科開始就追隨斯退士,并師從斯退士攻讀博士學位。作為英語世界著名的黑格爾研究專家,斯退士的存在對羅爾斯哲學思想的形成是決定性的。羅爾斯的朋友、哈佛大學哲學教授德萊本(Burton Dreben)說:如果抹去《正義論》的作者,讀者會以為這是一部從德語翻譯過來的英文版哲學譯著
這個說法轉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紀的任何一個偉大的歐洲哲學家一樣,羅爾斯是一個系統的哲學家。因此,如果我們沒有把羅爾斯整個理論以及他同其歷史先驅的關系放在一個較大語境中來考察,就難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觀點。在方法和風格上,羅爾斯都擺脫了分析傳統。(他的朋友伯頓?德萊本曾經將羅爾斯整體論方法同黑格爾方法進行比較,并在談到《正義論》時說道:‘它讀起來像是從德語譯過來的。’)”見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頓?德萊本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評論,是因為黑格爾哲學通過斯退士深刻地影響了羅爾斯,以至于《正義論》的結構框架同黑格爾《邏輯學》的結構框架形成了一種呼應關系。羅爾斯有意無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邏輯結構來組織《正義論》的主要論題,即《正義論》由三編組成,分別為“理論”、“制度”和“目的”;每一編下面又有三章組成,如第一編的三章為“公平的正義”、“正義的原則”、“原初狀態”;第二編的三章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額”、“義務和職責”;第三編的三章為“理性的善”、“正義感”、“正義的善”。這是一種典型的黑格爾式安排。其中第三編的三章很有黑格爾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東方哲學背景的哲學家。他指導羅爾斯學習黑格爾哲學,也學習神學、倫理學和道德心理學知識。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期間,羅爾斯跟隨斯退士研修德國古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和康德哲學。羅爾斯有意隱瞞了與斯退士的師生關系,但羅爾斯通過斯退士仍然同黑格爾哲學聯系在了一起,雖然羅爾斯生前很少談起斯退士,也沒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謝甚至提到這位老師,甚至很少談起他同黑格爾的關聯。一旦揭示了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黑格爾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們就更容易看清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歐洲大陸哲學的因素,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因素。
羅爾斯“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羅爾斯的正義理論直接指向社會基本制度。雖然羅爾斯明確表示,政治哲學的首要任務是探索設計社會基本結構的法理依據或道德基礎,是一項政治學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工作,他想以此強調自己秉承分析哲學傳統,但《正義論》開場白卻完全是黑格爾式的敘述。羅爾斯不僅進行事實描述,強調人們經由主觀價值判斷做出判斷,甚至整個正義理論得以構建都是基于歐洲大陸哲學的價值判斷。
羅爾斯故意隱去斯退士影響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點可以得到明確判斷,那就是在羅爾斯寫作《正義論》時,黑格爾是被美英分析哲學界完全無視的人物。羅爾斯只有通過隱去在其學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進而抹去其哲學思想中的黑格爾因素,使《正義論》顯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學兩大重鎮普林斯頓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維特根斯坦嫡傳弟子馬爾柯姆的直接調教下,在哈特和以賽亞?伯林等人影響下成就的政治哲學成果。
在斯退士和馬爾柯姆之間,在黑格爾和維特根斯坦之間,在宗教神秘主義和常識理性主義之間,羅爾斯做出了艱難但聰明的選擇,羅爾斯離開普林斯頓而投入馬爾柯姆的康奈爾哲學陣營懷抱即是明證。弗雷曼干脆說,羅爾斯只受到馬爾柯姆的少得可憐的政治哲學教導,幾乎是自學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經濟學,即功利主義哲學的社會科學基礎,淡化黑格爾傳統尤其是斯退士的影響。但弗雷曼還是不經意間披露了羅爾斯的秘密,即羅爾斯政治哲學的黑格爾起源。羅爾斯本人越是拒絕黑格爾,黑格爾哲學越是在他的哲學著作中無意識地呈現。他可以掩蓋他同斯退士的師徒關系,但他的哲學著作掩蓋不了那層關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國加州拉古鈉海灘去世,四年后,羅爾斯的《正義論》出版,羅爾斯在《正義論》序言中,提到了許多朋友、同事和老師對他的幫助,其中唯獨少了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斯退士。在整個《正義論》中,他只在一個腳注中提了一下:“有關這一點見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羅爾斯秘密的消極后果
正像當年馬克思指出黑格爾哲學中存在著“黑格爾秘密”一樣,羅爾斯政治哲學中也存在著“羅爾斯秘密”。羅爾斯秘密的客觀存在導致了一些消極的學術后果,主要表現為中國學者對羅爾斯正義原則和其他思想的誤讀,有些誤讀較為嚴重,已經產生消極的影響。鑒于正義原則在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關鍵地位,本文在此對由羅爾斯秘密導致的誤讀的具體表現只是點到為止(至于由這種誤讀產生的其他后果,將另文論述):如果說中國的羅爾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譯為“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12]56,把短語“total system”或詞語“system”譯為“體系”,一開始就把《正義論》中文讀者對第一個正義原則的理解引入了誤區,羅爾斯本人負有一定責任,那么,當羅爾斯在回應哈特的批評從而棄用“system”術語后,用來表述第一個正義原則至關重要的術語“scheme”仍然被譯為“體制”[13]70、“圖式”[10]5或“體系”[14]47,就不再是羅爾斯的責任了。同樣,在譯介羅爾斯原著的翻譯實踐中,短語“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譯為“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14]47,短語“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譯為“平等的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圖式”[10]5,短語“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譯為“一種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適當的體制”[13]70,這些譯法都偏離了羅爾斯想要表達的意思。這些表述方式也進一步證明了中國羅爾斯研究者已經深陷入羅爾斯陷阱之中而難以自拔。其實,在這里,無論“system”還是“scheme”,都只是量詞,而不是名詞。羅爾斯對“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證。同樣,在討論第一個正義原則時,“scheme”不能譯為“體系”、“圖式”或“體制”,而應譯為“組合”、“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譯為“一套最廣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則譯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羅爾斯在1971年《正義論》中第一次表述第一個正義原則的恰當中文應當是:“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享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那種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類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義理論基本內涵一道,研究羅爾斯正義理論或政治哲學的思想來源是羅爾斯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筆者的考察,羅爾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當代不甚重要的哲學家的關系。羅爾斯在談到《正義論》的寫作動機時,只說自己的工作是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論傳統的繼續,有意回避我們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對其思想形成的決定性影響。羅爾斯這種舍近就遠的做法誤導了羅爾斯政治哲學思想來源的研究者。
五、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的結論是:第一,羅爾斯正義理論有著清晰的分析哲學來源。羅爾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關系的緊密性超過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盧梭和康德的關系,即使從政治哲學史上來看,他同休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關系,與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盧梭和康德的關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當代經濟學理論是影響羅爾斯正義理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們無法全面展示羅爾斯政治哲學同當代經濟學的關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話足以呈現這種關系的基本輪廓。他說:“1990年,羅爾斯在接受《哈佛哲學評論》訪談時說,完成博士論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開始搜集與后來的《正義論》有關的筆記。在這個時期,他師從鮑莫爾學習經濟學,認真研讀了保羅?薩繆爾森的一般平衡理論和福利經濟學、希克斯的《價值和資本》、瓦爾拉斯的《純粹經濟學要義》、弗蘭克?奈特的《競爭倫理學》以及馮?諾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論。”[5]13
第三,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有其深刻的思想來源和神秘之處。羅爾斯以經濟學為武器,以分析哲學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義為批判對象,解決基本自由的問題,將自己與社會契約論傳統聯系起來,構建起完善的正義理論。除了在方法論上部分繼承分析哲學傳統,無論在行文結構、價值判斷或者是正義理論的構建方面,都具有黑格爾風格。黑格爾這位巨人很大程度啟發了羅爾斯正義理論的構建。在《我的教學工作》(1993)未公開發表的說法中,羅爾斯提到在《正義論》中他最喜歡的是第三部分,討論道德心理學的部分,這恰恰是從黑格爾和斯退士那里獲得的部分。
第四,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羅爾斯在《正義論》發表之初便說明這一理論得益于黑格爾,那么這本書也許會失去許多讀者,至少它將無法進入一流哲學評論家的眼中。當然,這只是一種猜測。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本來交叉重疊,學習兩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面對大陸哲學尤其是黑格爾思想被摒棄的情況,羅爾斯或許在大陸哲學和分析哲學之間做了艱難選擇,運用分析哲學外衣,巧妙隱藏大陸哲學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們試圖揭去羅爾斯分析哲學的外表,揭示其深層的德國古典哲學根源,尤其是一直隱藏其中的黑格爾因素,以表明羅爾斯哲學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歐洲大陸的傳統。如此,長期以來在羅爾斯和桑德爾、泰勒、麥金太爾、羅蒂等人之間的爭論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來那樣是學派與學派的爭斗,而更像是同一個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爭”。這一家族的家長有時是康德,有時是黑格爾,有時則是馬克思。無論家長是誰,它顯然有著純正的歐洲大陸血統,而與英美分析傳統無涉。如此,羅爾斯學說中的實用主義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現。一般來說,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之間有一條明確的鴻溝。分析哲學反對黑格爾,實用主義則對黑格爾充滿好感,黑格爾成為區分分析哲學和實用主義的一個重要標準。然而,羅爾斯距離黑格爾并不遙遠,離實用主義也不遙遠,因此,從深層來說,羅爾斯是一位地道的歐洲大陸哲學家。
總而言之,由于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羅爾斯本人的主觀原因,羅爾斯沒有明確地澄清他個人的思想來源。羅爾斯政治哲學吸收和借鑒了德國古典哲學、英美分析哲學、社會契約論、功利主義政治學、當代經濟學等眾多思想成果,呈現出從洛克、休謨、盧梭、康德、黑格爾(斯退士)、馬克思到維特根斯坦(馬爾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來源。其中,擺脫基督教的影響成為羅爾斯思考社會正義問題的邏輯起點,黑格爾哲學為羅爾斯構思正義理論提供了體系框架,分析哲學為他論證正義理論中的諸多原則提供了精細的方法論指導,當代經濟學為羅爾斯解決正義問題提供了可操作的實踐路徑。由于羅爾斯本人有意隱瞞其中某些思想來源,尤其是隱瞞同黑格爾和斯退士的關系,形成了“羅爾斯的秘密”,導致中國學者誤讀了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進而誤讀了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因此,中國的羅爾斯研究要想精確地把握其正義理論,必須從準確而全面地理解羅爾斯的思想來源開始,尤其是要注意羅爾斯政治哲學中的經濟學因素,否則,仍將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淺薄層次。
[參考文獻]
[1][英]艾耶爾: 《語言、真理和邏輯》,尹大貽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A.J.Ayer,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trans. by Yin Dayi,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1.]
[2]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張國清: 《譯者序:德性就是主觀的法》,見[美]羅爾斯: 《道德哲學史講義》,張國清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3年。[Zhang Guoqing,″Preface for Chinese Edition: Virtues Are Just Subjective Disciplines,″ in J.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 trans. by Zhang Guoqing,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4]R.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4,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5]S.Freeman, Rawls, London: Routledge, 2007.
[6][英]鮑桑葵: 《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汪淑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B.Basanque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trans. by Wang Shuju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7][德]黑格爾: 《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trans. by Fan Yang & Zhang Qita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2.]
[8]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J.Rawls,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S.Freem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美]羅爾斯: 《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trans. by Wan Junren, Nanjin: Yilin Press, 2000.]
[11][美]羅爾斯: 《簡論罪與信的涵義(兼〈我的宗教觀〉)》,左稀、仇彥斌、彭振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J.Rawls, A Brief Inquiry into the Meaning of Sin and Faith (with ″On My Religion″), trans. by Zuo Xi, Qiu Yanbin & Peng Zhen,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2010.]
[12][美]羅爾斯: 《正義論》,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8.]
[13]姚大志: 《羅爾斯》,長春:長春出版社,2011年。[Yao Daozhi, Rawls, Changchun: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2011.]
[14][美]羅爾斯: 《正義論(修訂版)》,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J.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 trans. by He Huaihong, He Baogang & Liao Shenbai,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9.]
[15]J.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篇5
關鍵詞:金林南;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范式的哲學沉思;讀后感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4)05-0011-02
金林南老師是河海大學學院一位年輕的“70后”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范式的哲學沉思》于2013年春季出版。筆者有幸在是年秋天捧在手中拜讀并求知若渴地在兩天之內把它讀完,作為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普通一線教師,不禁有一種渾身通透又躊躇滿志的感覺。據個人經驗而言,一直以來,還沒有看到一本著作能把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進行過一次如此完整而深入的哲學審視和分析,其認真的態度和筆者無法望其項背的學術高度令人敬佩。
一、簡介
在書中,金老師主要是借助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的“范式”理論,從哲學的高度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從理論到實踐、理想到現實,進行了邏輯與歷史的雙重思考,為這個誕生于實踐的學科在學術性與科學性的建構過程中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與指導,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
二、寫作目的與基本框架
在緒論中,作者首先介紹了美國史學家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論,繼而指出此理論“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基本問題的反思具有巨大的方法論意義”。接著,便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范式研究的現狀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最后明確提出了“本書任務”:一是“構建思想政治教育哲學”,二是“深思思想政治教育的本體”,三是“奠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認識論”,四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基本理論”,五是“創設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研究范例”。
整本書的框架即是在“本書任務”的基礎上確立的:第一章是“哲學精神與思想政治教育哲學”,主要考察了哲學精神的時代變遷,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現象及其哲學診斷,得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哲學的貧血”,并探討了“何謂思想政治教育哲學”。這一章主要為后面的論述奠定了理論基礎,讓讀者把握了本書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角度。第二章是“思想政治教育本體論”,先是介紹了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研究概況,現實地揭示了學界在思想政治教育定義和本質屬性上的爭議,同時分析了爭議的原因。把思想政治教育實踐的歷史和今天,以及人們對于其歷史和今天的認識掰開了、揉碎了,進行審視,并在此基礎上指出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思維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本體沉思的思維方式”,同時提出超越現有研究局限,為思想政治教育創新性的設定一個新的理論假設――意識的政治;在后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質的哲學沉思”中,結合中西方歷史現實與理論研究成果,對思想政治教育本質定義和內涵進行了闡釋,然后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內部矛盾的規定性,即政治與教育、政治與思想的矛盾及其發展。第三章是“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認識論”,作者首先界定了幾個基本概念:學科,認識論及思想政治教育學科認識論,繼而展開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屬性和學科方法論的哲學思考,與第二章的側重歷史分析不同,這里主要是進行理論論述,從根本層面來考察作為一門學科的思想政治教育。
后面的兩章則較多從經驗層面和建構層面來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第四章是“思想政治教育過程哲學”,第五章是通過一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來探討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首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缺失及其原因,然后針對現實的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理論與實踐的矛盾進行審視與追問。
從整個著作來看,作者憑借扎實的理論功底和廣博的知識儲備,以一種非常積極、負責、誠懇的態度,從縱橫兩個維度對思想政治教育的過去與現在、理論與實踐進行了一次徹底的哲學剖析。其主要構思是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門現實存在的學科,并用范式理論來審視這一學科,企圖在其現實運行的各種矛盾中完善這一學科。因為,從目前的事實來看,從實踐中誕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書中對學科和學科范式的定義,其學科屬性是“虛弱”的,學科體系是不健全的。
本書的幾大優點可歸納如下:
1.理論分析深入,這緣于作者深厚的理論功底。通過仔細閱讀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既具備了較高的哲學素養,對近現代哲學派別和大師們的基本理論主張都爛熟于心,同時還通曉各具體學科的理論與知識架構,如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等,也包括現實教育工作中的一些操作層面的知識與原則,這些在書中隨處都有體現,這使作者可以從學科“范式”理論入手,以哲學的思維進行思考和分析。雖然讀來并不容易,但是讀過之后卻使人有種深刻、通透之感,使那些散落于頭腦中卻經常困擾筆者的一些問題有了理論的梳理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