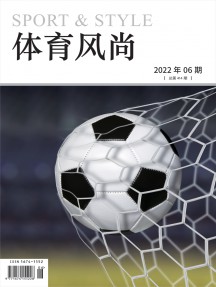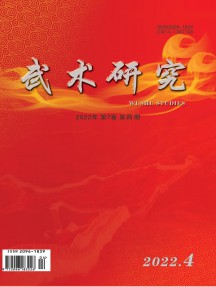競技體育的殘酷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02 17:22:27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競技體育的殘酷,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11月7日,帶著崇敬的心情,黨支部全體黨員奔赴白河三苦精神教育基地展館,開始了為期一天的參觀學習活動。
白河縣地處秦巴山區腹地,山大溝深,地碎土瘦,自然匱乏,環境惡劣,是國家級貧困縣,曾有專家論斷為不宜于人類生存的地方。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面對困境,勤勞勇敢的白河人民沒有聽天由命,在歷屆縣委、縣政府的帶領下,勇敢的向貧窮和落后宣戰,奏響砌“石坎坎”、端“金碗碗”之歌,堅持修田造地20多年,相當于7個萬里長城的石坎,在陜南土石山區率先實現人均一畝基本農田,初步解決了人民群眾溫飽問題。領導苦抓、干部苦幫、群眾苦干的白河“三苦精神”,是白河縣幾十年堅持不斷治山創業的經驗積累。在這種精神的引領下,白河縣不斷取得了經濟發展、生態優化、人民富裕的輝煌成就。
一幅幅生動的畫卷,一張張催人淚下的照片,無不向我們昭示著三苦精神的精髓。作為一名黨員教師,一名正處于事業爬坡期的青年教師,我們不能不為這種精神所打動。反觀教育,教學上何嘗不需要這種三苦精神呢?“領導苦抓,教師苦教,學生苦學”是一種工作作風,是一種工作狀態,更是一種學習風氣。
三苦是一種責任意識。教師要以高尚的職業道德、良好的敬業精神和強烈的工作責任心,認真做好教育教學工作和各項常規要求,努力使自己成為學生歡迎的嚴師、名師。學生要充分認識到學習不僅是自己的項義務,更是一種責任。對家長含辛苦哺育自己長大,千方百計培養自己成才的責任;對老師孜孜不倦教誨,廢寢忘食工作的責任;對自己生命價值和未來錦繡前程的責任。
篇2
馬飛,寶雞文理學院體育系講師,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體育教學與訓練。
(寶雞文理學院體育系,陜西 寶雞 721013)
摘 要:
結合競技體育中悲劇事件的發生現象,從悲劇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提出“心理距離”學說與競技體育悲劇理論,在此基礎上,剖析了競技體育悲劇的崇高感、、主體情感活動的動態平衡性與高峰逆轉以及競技體育悲劇的“凈化”和“領悟”的作用,進而提出悲劇精神是競技體育悲劇的生命張力。
關鍵詞:悲劇;悲劇心理學;競技體育悲劇
“悲劇比任何一種戲劇更容易喚起道德和個人的情感,因為它是最嚴肅的藝術,悲劇描繪的激情是最基本的,可以毫不例外地感染一切;它所表現的情節一般都是比較可怕的,而在人們可怕、恐怖和失敗的事情面前往往變得嚴肅而深沉。”[1]悲劇的意義決不是單純展示價值的破碎,從而給人留下一段傷感苦澀的回味,而在于通過展示悲劇英雄對不幸命運的抗爭,使人看到一種更高的價值力量,同時使人感到一種浩氣長存的生命力。“悲劇的要素不只是災難,還有抗爭。悲劇精神就是悲劇主人公所表現的,為實現某種美好價值而同不幸命運抗爭的奮斗精神和犧牲精神。悲劇英雄們以自己的奮斗犧牲(當然,不一定指犧牲生命)換來了更高價值的尊嚴,正因為如此,任何好的悲劇總能讓人領略到一種凝重、莊嚴、悲壯而崇高的美。”[2]競技體育從一誕生,就注定了悲劇的產生,競技體育比賽是殘酷的,有成功就有失敗,有鮮花就有汗水和淚水。競技體育的魅力就是悲劇人物面對挫折、困難、極限,以非凡的力量、堅韌的意志、頑強的精神戰勝對手、戰勝自我的精神。“悲劇美就是指人在遭遇到苦難、毀滅時所表現出來的求生欲望、抗爭中所顯示出來的旺盛的生命力,以及自我保護能力的最大發揮,也就是說所顯示出的超常的抗爭意識和堅毅的行動意志。因為在這種符合人生的抗爭與超越中,主體的人格力量得以提升,人的本質力量得以超常地展現。”[3]本文從悲劇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深層次剖析了競技體育悲劇的實質。
1.“心理距離”學說與競技體育悲劇
“心理距離”說可以在德國美學中找到根源。但是把“距離”的概念講得最詳盡的是英國心理學家愛德華布洛的文章《作為藝術中的因素和一種美學原理的心理學距離》。布洛認為“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系是“切身的”,客體能強烈地被吸引或反映出主體深層的本能,主體必須通過自然的天賦和后天反復的訓練具有一定的藝術天賦。”[4]競技體育是以競賽為主要特征,以創造優異成績,奪取勝利為目標的社會活動。心理距離應該是悲劇心理學的基礎。用“心理距離”說來觀察悲劇就會發現,悲劇是通過真人來表現的,因此在保持距離上它有先天的不利條件。但是這種不利條件卻被悲劇的種種手法彌補起來了。藝術的程式化、人為化、抒情化,安排的超自然氛圍,以及非現實而具暗示性的舞臺演出技巧,從而把現實生活“過濾”了、理想化了,悲劇利用這些“距離化”因素,給人提供了生活本身所不能提供的壯麗和美。在競技體育比賽中,主體運動員通過先天的運動天賦和后天的刻苦訓練,把人體的運動潛能發揮到極限,反映出主體人征服自然、挑戰極限、戰勝困難的決心。但是,競技體育是殘酷的,因為賽場上冠軍只有一個,大多數人最終都要以失敗告終。競技體育比賽猶如戲劇里的悲劇,運動員通過精彩的表演,把一部偉大的悲劇濃縮成可以表演、觀眾能看懂的一連串戲劇情節,通過“心理距離”,感受到競技體育悲劇強大的震撼力。
2.競技體育悲劇的崇高感
亞里士多德曾經深刻地指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為的摹仿”,“引起憐憫和恐懼來使感情得到陶冶”,具有“凈化”靈魂的教育意義。[5]悲劇的崇高感是人類特定的情感、意志和行動的構成體。[6]“崇高感是一種間接引起的,因為它先有一種生命力受到暫時阻礙的感覺,馬上就有一種更強烈的生命力開始醞釀,所以崇高作為一種嚴肅的情緒,能使人產生敬畏和崇敬。”[7]悲劇能夠使人的心靈接觸到崇高和莊重的美,能夠喚起人們心靈中崇高莊重的情感,能夠開啟人們的心靈之門,點燃一星隱秘而神圣的火花。競技體育作為一種挑戰自我、超越自我,追求人類“更快、更高、更強”的生命活動,它本身就孕育了無窮的魅力和生命的價值;無數的競技者,在體育運動中,贏得了愉快與幸福,并心甘情愿地為之流汗乃至流血。醫學家們計算,一個運動員在其運動生涯中流出的汗水是2000-4000kg,一般要超過他(她)體重的25-50倍。對平常人來說,是很難想象和接受的。為了超越前人和對手,實現自己的價值,運動員不僅要經過長期的、以戰勝自我為目標的極限強度訓練,而且還要承受創新、創難動作帶來的身體、生理和心理的極大壓力,甚至傷病的折磨和死亡。也許人們還記得在第20屆慕尼黑奧運會上發生的悲劇,也記得在第17屆羅馬奧運會丹麥自行車運動員死亡的悲劇以及在阿爾貝維爾冬季奧運會瑞士滑雪運動員死亡以及2006年多哈亞運會上,韓國47歲馬術選手金亨七在馬術比賽時墜馬而死的悲劇。運動員“傷殘”已經是一種悲劇了,但是,當透過傷殘的陰影,影射出人戰勝自我,挑戰極限的拼搏精神,從悲劇心理學的角度來說,它是由“悲”向“喜”的升華。“悲劇是在一場焚毀價值的大火中為一種新價值的誕生發放出生證。”[8]悲劇是遼闊無比的蒼穹,是充斥宇宙的暴風驟雨,是異乎尋常的英雄氣魄,是震撼心靈的狂呼吶喊……
3. 競技體育悲劇的
任何人生命中的痛苦、死亡都有某種程度的悲劇性因素,都要觸動人們心理深層潛伏的死亡意識,都要引起人的心理的恐懼與憐憫感。現代心理學證明,對自己生命苦難和死亡的恐懼,對別人的生命痛苦與毀滅的憐憫是人類一種原始情感的心理效應。“悲劇的心理效應可分為群和痛感群,群的各要素可以相互連接,呈現出一種趨向,共同構成一種綜合的體現。與此同時,痛感群中的各感情點也可以相互連接,從本質上呈現出一種審美的痛感。”[9]奧運會是展示人類“更快、更高、更強”的競技舞臺,也是品味喜怒哀樂苦辣酸甜的人生驛站,當有人站在最高領獎臺享受勝利的時,就意味著有人失意而歸,就意味著領獎臺某一個角落里又有一名悲情英雄的流淚,或許正因為如此,競技體育才會顯的那么令人激蕩,具有如此難以抵擋的魅力。和痛感是從奧林匹克運動母體中帶來的兩種情感。競技體育追求的最終目標是取勝,就必須帶來一種永恒的矛盾,競技體育不僅僅包含憐憫和同情,還包括導致愉快和振奮的“調解”,人們在欣賞競技體育的同時,還能獲得一種回味的。在競技體育比賽中,運動員展示的不僅僅是運動技巧和奧林匹克精神,而且,運動員的高昂的士氣、堅強的毅力等,比賽的投入和關注讓人敬畏,他們對勝利的渴望,振奮的精神,大聲的吶喊,讓人能真正的體會到競技體育帶給人們的。競技體育是殘酷的,當人們從悲劇中體味到獲得的時,就會被人類高尚、頑強的意志所折服。
4. 競技體育悲劇主體情感活動的動態平衡性與高峰逆轉
著名心理學家馬斯洛曾提出過一種“高峰體驗”的理論,其內涵主要指出,人在進入一種自我實現和自我超越狀態時可能會感受到一種極度歡樂的體驗。而且他認為,這種“高峰體驗的特征是瞬間產生,轉眼即逝的,因而往往逃過了人們的注意,使人們弄不清它的性質,但這樣的時刻到來時能產生強大的沖擊波,使人擺脫一切懷疑、恐懼、壓抑、緊張和怯懦”,而且“這些特征包括暫時的時空混亂感,驚奇和敬畏感,巨大的幸福感。”[10]顯然,馬斯洛把高峰體驗與情感的瞬間轉化放在了一起加以馬斯洛的“高峰體驗”論可以恰當地說明悲劇審美主體在情感中審美痛感到審美這一轉化過程,而且能很好地解釋為何悲劇審美高峰時主體會感受到一種痛感與相互交織的極大震撼。“審美主體在欣賞一部悲劇作品時,情感中會激起多少復雜的對立因素,這些對立性情感始終是處在一種動態平衡的運動狀態中的。” [9]“悲劇審美是一個時間序列里的心理活動過程,當審美主體在欣賞一部悲劇時,由于悲劇主人公的痛苦遭遇,致使審美主體在情感中激起了一系列屬于痛感群中的各類情感活動。”[11]大逆轉是足球比賽中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一幕,當一個隊以絕對的優勢處于領先地位時,雙方主體的情感活動基本上處于一種動態平衡,但是當這種動態平衡被打破,出現高峰逆轉的時候,觀眾將會體會那種逆轉的刺激和緊張的。在第三屆法國世界杯上,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巴西隊與波蘭隊的比賽充滿了戲劇性,這也許是世界杯決賽階段歷史上最精彩最富戲劇性的大翻盤。1938年,“足球王國”巴西作為南美唯一的代表參加了在法國舉行的第3屆世界杯賽,也正是在本屆杯賽上他們開始展露出強大的實力。在爭奪前8名的戰斗中,巴西隊與歐洲勁旅波蘭隊碰在了一起,這場比賽是在雨后泥濘的場地上進行的。開賽后波蘭隊攻勢凌厲,射門命中率極高,不久就以5比0遙遙領先對手,波蘭隊看似已經勝券在握,孰料巴西隊穩住陣腳之后漸漸穩定了情緒,在泥地上打起了流暢的地面進攻,很快就反過來控制了場上的局勢。在剩下的時間里竟然也回敬了對手五球,最終以6球逆轉戰局。可以說,這種從痛感高峰點上瞬息轉化為一種的過程,正是競技體育悲劇審美主體情感的高峰逆轉過程,也是競技體育的魅力之所在。
5.競技體育悲劇的“凈化”和“領悟”
“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悲劇的產生來源于人覺得有價值的東西被泯滅了。價值的毀滅,會引起悲劇意識,悲劇對情緒的凈化在于把憐憫和恐懼轉變為合于美德的思想感情。悲劇的心靈的凈化是繼共鳴之后而不由自主地達到調節精神、排遣情緒、去除雜念和提升人格的狀態,從而達到自我教育的效果。”[12]領悟是繼共鳴和凈化以后進入潛思默想、體悟人生、提升精神等過程的更高境界。與前兩種境界相比,領悟是接受者在共鳴與凈化的基礎上,對體育運動的內涵作出主動的思索和深刻的理解與體味;同時,共鳴常常是建立在接受者對體育信息一般認同的基礎上,凈化主要表現在接受者的精神舒暢和心靈的矯正,往往不能直接產生新的人生指向。而領悟則在思索和理解的前提下,能有效地豐富和擴充接受者的期待視野,使接受者主動發生一種積極的人生向往。當欣賞完一場競技體育悲劇時,比賽場景還會縈繞在腦際,思想情感仍會波動于心間,情趣、意境可能會引起再三回味,甚至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于腦際,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著自己的道德情操、言談舉止和審美追求,這種心理狀態即為回味與延留,這既體現了接受者的思想變化,又對其審美趣味、精神氣質、以及人格規范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是體育運動產生直接社會效益的重要方式。我們的肉體需要體育,我們的精神更需要體育,特別是在技術理性為尚的今天,人類的精神需要藝術和體育這兩種東西來實現心靈的凈化與皈依。與此同時,我們的肉體還需要體育為之支撐起生命之帆.于是,體育就被賦予了更為豐實的存在價值,它的功能也就不言而喻。
6.悲劇人物與競技體育悲劇的生命張力
“悲劇的誕生以酒神的受苦為題材,酒神一直是悲劇的主角。悲劇人物表現的是酒神的智慧,只有以大苦大難、厄運為代價,毀滅一切舊的法律、道德、秩序,才能建立一個新的世界。”[13]尼采認為:悲劇是一種生命論悲劇觀,它通過悲劇人的犧牲、毀滅,喚醒人類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使世界充滿“嬉戲著痛苦的刺激”的生命力。競技體育比賽是殘酷的,冠軍只有一個,獎牌只能掛在少數人的胸前。這說明了競技體育的殘酷性,在競技場上,失敗是競技體育永恒的主題,悲劇人物將是競技體育悲劇的“夢工廠”,
即使是冠軍,在人類自身極限面前,永遠也是失敗者,而且冠軍的不永恒性,也決定了冠軍的悲劇命運,今天的榮譽可能將成為明天跌入低谷的殉葬品。冠軍的短暫性與悲劇的永久性共同演繹著競技體育悲劇,這就是競技體育的魅力之所在。施萊格爾說的好,“人性中的精神力量只有在艱難困苦中,才充分證明自己的存在。”“正如人的偉大只有在艱難困苦中才顯露出一樣,只有與命運觀念相聯結才能產生悲劇,因為悲劇的本質是表現悲劇人物的壯麗,激發人類的生命力感和積極努力向上的意識。”[12]
悲劇不僅表現生活的肯定,并且也表現生活的否定,但必須是悲劇性質的否定。 競技體育根植于不斷毀滅而又不斷超越的奧林匹克文化,其悲劇意識正是人類生命的根基性意識,也是奧林匹克運動文化之精髓所在。
[參考文獻]
[1] 朱光潛著. 悲劇心理學[M].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5: 45.
[2] 尤• 鮑列夫[蘇]. 美學[M]. 馮申. 高叔眉譯.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77
[3] 樓昔日. 美學導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166.
[4] 德拉庫瓦. 藝術心理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社,1927:27.
[5] 朱光潛譯. 西方美學史[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69.
[6] 王福仁. 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 [J] 江蘇社會科學, 2001,(1) : 116.
[7] 康德著. 論優美感與崇高感[M]. 北京:商務出版社,2003:13.
[8] 章輝. 悲劇精神與悲劇意識[J]. 文藝研究,2001:(5):150.
[9] 胡澤球. 論悲劇的的產生[J]. 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4,(5):66.
[10 楊清. 心理學概論[M]. 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56.
[11] 楊春時. 審美理解與審美同情[J]. 廈門大學學報,2006,(5):45.
篇3
一
運動員在體育比賽中流淚是很常見的一幕。但在電子競技的比賽中我們似乎很難見到。不過這次WCG的比賽中,小編我“有幸”見到了兩次這樣的場景,雖然哭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是英雄所留下的淚,都是讓小編我足以動容的眼淚。
敗者組決賽中,LX和Pi這對冤家又一次碰面,不過和去年爭奪冠軍有所不同,這次比賽是爭奪三四名的比賽,而殘酷的是,第四名將無緣世界總決賽。最后的結果相信大家已經知道了,那就是LX輸掉了比賽,在Pj離開比賽場地后,LX再也沒有掩飾內心的悲傷,痛苦的哭了起來……
最后的決賽中,66和F91一直打到最后一局,最終F91遺憾的輸掉了比賽,而66獲得了中國區總冠軍。比賽結束后,66難掩心中的喜悅,眼圈紅了,并和F91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淚水見證了這感人至深的一幕……
二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想想前不久結束的PGL比賽,LX在失利后并沒有這樣傷心的哭泣,而且想想其他比賽中,選手的淚水也并不多見。尤其是在比賽這么多的現在,難道輸一場比賽對選手這么重要嗎?
雖然目前的電子競技比賽并沒有人來分級評定,但在每一個人心中,比賽其實都有著自己的特征和特殊含意。PGL好像和專業化相匹配,ESWC好像和檔次相融合,G聯賽能讓人放松神經。而WCG是選手心中,尤其是星際選手心中最高的追求和很多玩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園。
WCG是一項偉大的賽事,是他最早詮釋了電子競技的概念,讓電子競技登堂入室,而他最早的項目就是星際爭霸。歷史,讓這項賽事在星際爭霸選手的心中占據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而隨著電子競技的發展,真正的世界性星際爭霸比賽就只剩下了WCG。所以無論是為國爭光,還是實現一個星際選手最高理想也只能在WCG這個舞臺上了。
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對于身經百戰的LX和66來說,失去和得到WCG的冠軍對他們來說是那么的重要。為什么他們在這一刻都會不約而同的選擇用眼淚來表達自己內心的苦楚和喜悅。
三
記得在OSL的宣傳片中,最讓人動容的一幕是Nada一邊哭泣一邊接受采訪,而在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會感動,哪怕你并不知道他是誰。這就是體育的魅力,但也是體育的殘酷。
因為這一刻雖然感人,雖然催人淚下,但他也意味著一個道理,成王敗寇。LX和66的眼淚雖然都讓我們難忘,但冠軍卻是66的。一段時間以后,人們只會記住66,而不會記住LX。這就是電子競技,這就是體育。
現在,有人說電子競技是娛樂產業,或者說應該走娛樂化路線,但這樣的說辭卻忽視了電子競技和其他體育項目共同的特點,也忽視了電子競技和所謂娛樂化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所謂的娛樂產業中,無論娛樂的人還是被娛樂的人,都沒有什么標準去衡量一個人的勝敗,在娛樂產業中成功的標準是多元化的。能拍商業電影和能拍藝術電影的導演都能成為偉大的導演。但電子競技不一樣,電子競技輸就是輸,敗就是敗,一個人長得再帥,再有魅力,人氣再高,包裝的如何如何,道德上多么完美,但沒有成績,那所有的一切都是沒用的。而在娛樂產業中,他就可以“成功”。
四
一位美國學者在他的《體育社會學》中這樣說:體育與娛樂的結合是體育商業化的必然,但所有的娛樂僅僅改變的是賽場外的人和事,體育本身的目標和結構是不可被改變的。
篇4
我和眾多網友一起觀看了傅園慧的直播,這場有1000萬人圍觀的直播里,“洪荒少女”一直在吃蛋糕,絲毫沒有顧忌形象。甚至于,這場早在幾個月前定下的商業直播里,直播主持人一直在引導傅園慧念廣告,粉絲們則拼命花錢送禮物,而這位耿直少女卻一直在重復“別送東西了”。直播的氣氛有些尷尬,風格卻又格外“傅園慧”。
傅園慧為什么會火,很多媒體將之歸結于,傅園慧脫離了中國運動員以往給人的刻板印象,將其他運動員不敢說的先說出了口,所以火了。然而事實上在社交網絡上,國外網友都將傅園慧視為“網絡紅人”,美國脫口秀主持人Ellen給“洪荒少女”做了個惡搞動圖,眾多國外網友把菲爾普斯的“死亡凝視”和傅園慧的表情包放在了一起做成了熱圖。 在BBC專門介紹傅園慧的文章中,將“洪荒之力”翻譯成了prehistoric powers。
這不僅僅是一場中國網民的狂歡,不僅僅是中國式獨有的喜歡。元氣少女傅園慧的受追捧與其說是體制的松動,社會環境的包容,不如說是互聯網新媒體時代的產物。不管是刷遍了網絡的“洪荒之力”,還是史無前例的直播面對網友,這種平視以及高效的互動下,這樣的“個性”才會被接受,這樣的“個性”才會轉化為不需要包裝的商業推廣。
在中國,很長一段時間里,運動員的個性是不被需要的,商業價值是同運動競技成績掛鉤起來的。不管是傅園慧的同門師兄寧澤濤,還是國內運動員中商業運作最為成功的林丹,國內的體育明星想要在競技成績之外獲得更大的影響力,無一例外,需要橫跨體育圈,娛樂圈和時尚圈三個圈進行形象包裝運作。然而,并非每一個奧運冠軍都能被運作成為體育明星,而傅園慧是目前為止唯一一個憑借著互聯網就成功“跨圈”的體育明星。
Fan圈文化的擴大,愛國和追愛豆兩種感情結合又是這屆奧運會最大的特點,傅園慧被標簽成了段子手網紅,中國游泳隊的運動員們無一例外被刷成了耿直逗比化的“泥石流”,網友編的段子,剪輯的視頻里,中國的運動員們從以往的一種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被標簽化,轉化成了另一種被標簽化。
而1000萬人次的直播圍觀,已經能說明這場互聯網的“造星”在傅園慧身上顯示的商業價值了,可以想象奧運會之后她的商業估值會達到怎么樣的程度。
篇5
賽前就知道自己是陪太子讀書的,那光輝矚目的領獎臺是給別人搭建的,自己的成績無非是別人名次遞進時的基數,這個時候如對著采訪的鏡頭,說出那句經典之話:“貴在參與,重要的是戰勝自己。”那就是拿著涂了油彩的遮羞布這么一晃,就只剩下“光彩”了。語言的奇妙就在這里,就像討伐太平軍時,把屬下準備匯報給皇帝的戰況材料中寫到的“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雖說戰場的局面照舊,但卻用那支筆把一支草包的清軍“改造”成了頑強的隊伍,慈禧太后聽著也舒服多了,但剿滅太平軍卻不能用筆呀。
競技體育比賽要的就是名次,戰勝所有的對手,才能拿金牌,戰勝的僅僅是自己,連鐵牌也沒人給你發,如果我們圖的就是戰勝自己,完全可以在自家的庭院之中“較量自己”嘛,就不必“千里赴戎機”,費銀子,耗體力了。就像中國足球隊,球迷寵,收入高,素質差,卻自戀,他們從來不覺得自己在亞洲是弱旅,早就戰勝自己了,但就是戰勝不了別人,這樣的球隊國家還養著干啥?難道就為了給國人添堵嗎?讓他們玩“戰勝自己”不就行了嗎?那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戰勝對手。戰勝不了所有的對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讓所有的對手戰勝還沒有失敗感,又來一句“我戰勝了自己”,可你自己能辦奧運會,還是能辦世界杯呀,不能辦吧。這次奧運會國際友人們都來到了咱們的家門口,我們給人家的最高禮遇就是“戰勝”對手。運動場上讓人家尊敬你的前提就是你還是我的對手,被劍客擊中,被拳擊手打倒,都不會成為今后的敵人,反倒是那些“屢戰屢敗”的對手,你就是拿高價的出場費邀請人家“強者”來打一場熱身賽,人家都懶得來。
無論你是強者還是弱者,只要去參加競技體育比賽,就要想到:我就是為了戰勝對手才來的。戰勝不了所有的對手不是失敗,但戰勝一個對手也是一次勝利,千萬別把自己先當作了戰勝的對手,戰勝自己的事兒留著回家時再干。
競技體育不是鍛煉身體,伸伸腿彎彎腰,隨著音樂做體操。競技體育的精髓在于勝敗,如果只是一個強者的游戲,那么這項運動也無法長久,李永波有句名言:競技體育的殘酷,就在于它的標準就是勝敗。是啊,我們培養一個金牌奧運選手的資金在2004年大約是一億人民幣,如今就不止這個數了,不戰勝對手,還不如把那些錢都用來發展全民健身的群眾體育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