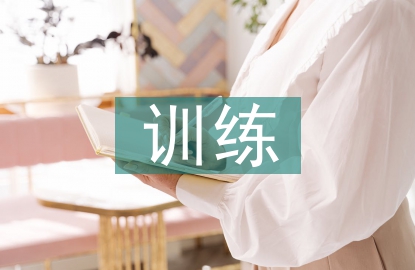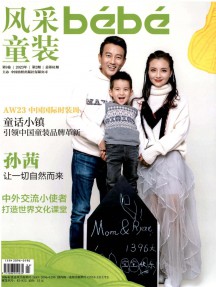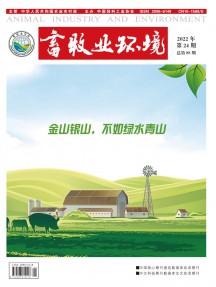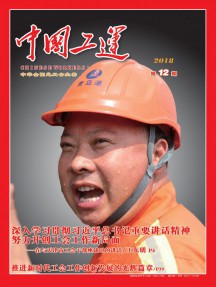關于交通的法律規定精選(五篇)
發布時間:2023-10-24 10:52:58
序言:作為思想的載體和知識的探索者,寫作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我們為您準備了不同風格的5篇關于交通的法律規定,期待它們能激發您的靈感。

篇1
【關鍵詞】交通肇事罪 財產抵刑 存廢
1997年《刑法》在借鑒1979年《刑法》規定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當時交通運輸業的客觀情況,進一步完善了對交通肇事罪的規定。而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出臺,則明確以司法解釋的形式規定了交通肇事罪的財產抵刑條款。這些有關交通肇事罪的財產抵刑條款解決了現實生活中的一些疑難案件,但與此同時,其也存在與我國刑法理論和基本原則相悖之嫌。
有關交通肇事罪財產抵刑的法律規定
《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第四條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傷五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二)死亡六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對交通肇事罪財產抵刑條款的質疑
通過《解釋》第二條、第四條的規定可以看出,發生交通事故時,在沒有造成人身傷亡而只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且肇事人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情況下,如果肇事人有能力承擔三十萬元以上或者六十萬元以上的賠償數額,肇事人就不構成犯罪或者雖然構成犯罪但不被從重處罰。同時,肇事人如果無能力賠償或者有能力賠償但沒有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或者六十萬元以上的,國家保留了追究的權力。犯罪數額作為定罪標準和量刑標準的情形在我國刑法典中是普遍存在的,但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定罪標準和量刑標準的情形卻是本解釋的首創。
對此問題,肯定說和否定說之間的爭論愈演愈烈。肯定說主張,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刑法謙抑原則的體現和出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考慮,對賠償損失的肇事人不以犯罪論處有利于社會和諧、生產發展,不存在不公平、不平等、不正義的問題,反而是對國家、社會以及受害人有益的做法。①否定說認為,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拿錢買罪、用錢抵刑”的做法,極大傷害了人們追求平等、正義的樸素情感,與刑法公平、正義的精髓相悖。②筆者贊成否定說的觀點。
首先,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對刑法謙抑原則的違反。刑法謙抑原則是指,當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發生時,在民法、行政法可以調整的情況下,盡量不動用刑法;只有當民法、行政法不足以遏制惡的行為時,才適用刑法。在《解釋》第二條第二款第三項和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的情形出現時,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被予以彌補后,雖然肇事人受到了一定的懲罰,但這對矯正行為人的行為來說是沒有實質意義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是預防危害社會的行為的發生,而這一目實現的決定性因素不只是盡量彌補行為造成的損失使社會利益恢復到犯罪前的狀態,更重要的是消除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使行為人不再犯罪。在交通事故發生且肇事人負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案件中,只要肇事人能夠賠償事故損失就不被定罪或者不被重罰的做法,為有錢人大開違法犯罪的方便之門,不僅不能遏制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而且會弱化人們的法制觀念,傷害法律的權威和尊嚴。
其次,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對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的違反。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是刑法典的基本原則,任何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人犯罪,都應當平等地受到法律的追究;《解釋》的相關規定,以肇事人的賠償能力為標準,對相同的肇事行為作出了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這樣截然不同的規定,從“立法”這一源頭上確定了適用刑法的不平等,造成了司法審判難以想象的尷尬。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各地區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均衡,人均占有的社會財富并不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定罪的標準也以財富多少來設定,必然會嚴重挫傷人們的法律情感。因此,《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和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嚴重阻礙了當前歷史條件下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必須予以廢除。
第三,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對主客觀相統一的刑法原則的違反。在司法實踐中,衡量一個客觀發生的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首先是看這一行為是否被刑法所禁止,其次是行為人在做出這一行為時主觀上是否有罪過,如果這兩個條件都被肯定,則行為構成犯罪,行為人被處以刑罰。將該行為認定為犯罪,是裁判者依據法律規定對客觀“惡”的否定;對行為人處以刑罰,是裁判者依據法律對行為人主觀“過錯”的譴責;對被判處的刑罰付諸于執行,則是在糾正行為客觀“惡”的同時,改造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使其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最終放棄再次犯罪的念頭,能夠重新回歸社會。如果說在定罪時側重于考慮客觀,著眼于行為侵害的法益的話(侵害的法益不同,成立的罪名不同),在量刑時則側重于考慮主觀,著眼于刑罰執行的實效(實際執行的刑罰種類及期限能否徹底改造犯罪分子的罪惡思想)。所以,《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和第四條第三項的規定,只看到肇事行為造成的客觀損害結果,只注重對客觀損害的恢復,而沒有看到肇事人的主觀過錯,不注重對肇事人“過錯”思想的改造,這種做法既不能準確定罪,也不能準確量刑,不僅起不到預防犯罪、遏制犯罪的作用,反而極易成為誘使犯罪再次發生的導火索。
最后,以犯罪人的無能力賠償數額作為罪與非罪、重罪與輕罪的衡量標準是對刑法典有關交通肇事罪規定的違反。為了讓相對穩定的法律能夠適應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需要,對法律進行解釋就成了解決法律的穩定性和滯后性這一對矛盾的捷徑。顯性的法律規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本身就已經清楚地表明了規定的含義,所以一般情況下不需要進行解釋。隱性的法律規定,由于其法律文字所涵蓋內容的不確定性,在司法適用的過程中極易引起混亂,所以必須進行解釋。但法律解釋都是針對法律規定而言的,法律解釋不該脫離法律規定而存在,法律解釋不是要將法律規定本身沒有的內容強加于法律規定。③從這一角度講,本《解釋》超越了刑法典有關交通肇事罪的規定,強行賦予了交通肇事罪本不含有的內涵。
現行《刑法》規定的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像其他所有的過失犯罪一樣必須有危害結果的發生才能滿足“罪”的成立,因為只有這樣,“惡”的行為才能達到應受刑罰懲罰的程度,才能與一般的民事、行政違法行為區別開來,所以刑法典將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方面界定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鑒于對財產抵刑問題的探討,這里僅討論“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這種結果。“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是交通肇事行為所造成的客觀危害,是一種現實存在的損害事實,也是交通肇事罪成立必需具備的客觀方面要件。而根據《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此處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客觀方面要件是“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可見,將“無能力賠償的損失數額”等同于“公私財產遭受的重大損失”,其實質就是將行為人的金錢賠償能力取代了犯罪行為造成的客觀損害結果而成為了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方面要件。④至此,交通肇事罪的客觀方面要件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并非是交通肇事罪的隱性規定,而是司法解釋強加于立法的。
此外,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法律責任,而且這兩種責任是不能互換的。⑤《解釋》第二條第一款第三項的規定,實質上就是在肇事人賠償了三十萬元以上損失后將刑事責任異化為民事責任的做法。還需要指出的是,使用外國的“易科制度”來闡釋本《解釋》的合理性也是欠妥當的。⑥“易科”僅僅是刑罰種類的轉換,并不涉及罪與非罪的轉化問題。
有關交通肇事罪的財產抵刑條款,從立法這一源頭就規定了適用刑法的不平等,既造成了司法適用過程中的混亂,也引起了人們對我國刑事法律規定的不滿,更是對公平、正義等法律理念的褻瀆,廢除交通肇事罪的財產抵刑條款是我國刑事法律制度不斷向前發展的必由之路,必將得到人們的擁護。(作者單位:唐山學院文法系)
注釋:
①⑥曹小清:“關于交通肇事罪若干問題的探討”,《法制與社會》,2009年1月(上),第368~369頁。
篇2
民 事 判 決 書
(2006)甬民三終字第26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住所地寧波市江東區桑田路643號。
訴訟代表人周波,總經理。
委托人(特別授權)竺浩興,浙江金漢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高峰,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漢族,住安徽省霍邱縣潘集鄉街道。
委托人(特別授權)蔡士勇,浙江紅邦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人(特別授權)姚善挺,浙江紅邦律師事務所律師。
上訴人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為與被上訴人高峰保險合同糾紛一案,不服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二初字第486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05年12月20日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06年1月17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的委托人竺浩興,被上訴人高峰的委托人姚善挺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判決認定,2004年2月29日,原告將其所有的牌號為皖N55851自卸貨車,以原告和徐澤峰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車輛保險。保險期限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第三者責任險峰的賠償限額為50萬元。2005年1月7日21時許,原告駕駛該保險車輛在寧波市鄞州區姜山環鎮路發生保險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經交警部門認定,本案原告需對該起交通事故承擔主要責任。2005年3月18日,死者家屬向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后經該院判決,本案原告應賠償死者家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被撫養人生活費、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的損失計270928元。2005年8月3日,被告作出機動車輛保險賠款理算報告,同意支付第三者責任險74513.60元。后該款項由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執行局擔存后交付受害人家屬。
原審法院認為,原、被告間的保險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合法有效。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本案屬合同之訴,雙方的權利義務應依合同約定。原、被告簽訂的保險條款第四條、第三十五條約定:“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支付的賠償金額,保險人依照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閎法律法規和保險合同的有關約定給予賠償”;“保險車輛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中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在保險單載明的方式及賠償限額內核定賠償金額”。對于上述條款,原、被告理解不一致。原告認為,此所謂的“現行法律規定”即指“事故發生時”正實行的法律法規,而該起交通事故的發生時間為2005年1月7日,而此時國家關于計算人身損害賠償數額的法律依據是《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故本案應以此核定賠償金額。被告則認為,所謂的“現行法律指定”,按照雙方簽約時的意思表示,應指合同簽訂當時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雙方亦未在2004年5月1日《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施行后,相應變更保險合同,故本案應以《道路交通奮不顧身處理辦法》核定賠償金額。原、被告簽訂的保險合同的條款及所附的保險條款均系被告提供的格式條款,對格式條款的理解發生爭議時應當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釋,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本案所爭議的格式條款系被告提供,現雙方對該條款的含義有不同的解釋,故按照合同法關于格式條款的解釋的規定,應當采納對格式條款提供方即被告不利的解釋。另原、被告簽約時,《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頒布,原、被告已將第三者責任險的限額提高至50萬元,故“現行法律規定”應理解為《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現原告依該解釋規定的賠償標準及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號民事判決書依該解釋的相關規定判定的賠償數額作為計算依據要求被告賠款,理由成立。但原告提出的賠償額的計算方法不妥,應以合同約定的理賠計算方法為準[即賠款=應負賠償金額270928×(1-免賠率5%)-自負額1000元]。現被告已實際賠付74513.60元,故對剩余部分應當賠付原告。對于被告辯稱原告未實際向受害人家屬賠付該款,所以該賠付額尚未確定,被告無需賠付的主張,因該賠付額已經生效法律文書判決,是確定的,必須支付的,且原、被告之間的合同并未約定須實際賠付后才能理賠,故被告辯稱理由不足,不予采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第六十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原審法院于二00五年十一月八日作出如下判決:一、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支付原告高峰保險金181868元(已扣除原告自負額1000元及5%免賠率及被告已賠付的74513.60元),限于判決生效后七日內履行完畢。一審案件受理費5148元,由原告負擔1元,被告負擔5147元。
宣判后,上訴人原審被告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寧波分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被上訴人至今未履行第三者死亡事故的民事賠償判決,其實際賠償額尚未確定,故其要求上訴人賠付該民事判決確定的賠償額,依據不足,且不符合理賠程序及保險理賠原則;二、原審認定雙方簽訂的保險合同的保險條款第四條、第三十五條中的“現行法律規定”應理解為事故發生時的法律規定即《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是沒有事實基礎的。按照雙方簽約時的意思表示,應該指簽約當時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而不是尚未施行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依法駁回被上訴人的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高峰辯稱:一、被上訴人應向被害人賠償的數額已由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號生效判決所確認,且雙方的保險合同也未約定被上訴人需實際賠付后,才能要求上訴人理賠,而上訴人已實際履行支付74513.60元的事實,也證明了上訴人提出的被上訴人未向被害人實際賠款而不能要求保險公司賠款的觀點,不能成立;二、根據保險合同第三十五條約定,保險車輛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中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及保險合同的約定核定賠償金額。該條款中的“現行法律規定”應指“事故發生時”施行的法律法規,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即使上訴人對該條款有其他理解,但由于上訴人系格式保險合同的提供者,根據有關法律規定,應對該條款作不利于上訴人的解釋。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經審理查明的事實與一審判決認定的事實一致,且睛訴人在上訴中也不持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簽訂的《機動車綜合保險合同》合法生效,雙方應按約履行。合同履行中,雙方對保險條款第四條、第三十五條中有關“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的理解產生異議。本院認為,本案保險條款系上訴人提供的格式條款,在當事人對合同條款的理解有爭議時,應當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詞句、合同的有關條款、訂立合同的目的、交易習慣以及誠實信用原則,確定該條款的真實意思。雙方在2004年2月29日簽訂該保險合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分別于2003年10月28日、2003年12月26日頒布,雖尚未實施,蛤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已經實施,原來作為處理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隨著新法的實施已經廢止,被上訴人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經法院判決向被害人賠償的。投保人投保目的是為了轉移風險,在發生保險事故后能盡可能的減少自身的損失,被上訴人投保第三者責任險的賠償限額為50萬元,在其與上訴人簽訂保險合同后,有理由相信在出險后,能得上訴人全面的理賠。再從誠實信用原則出發,作為保險公司的上訴人,對法律有較強的認知能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經頒布,且即將實施的情況下,仍在保險條款中規定容易引起歧義的“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且未向被上訴人明確說明該條款所指的具體法律法規,系未盡充分的注意及說明義務,結合保險條款第三十五條“保險車輛發生第三者責任事故時,按國有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中規定的賠償范圍、項目和標準以及保險合同的規定,在保險單載明的方式及賠償限額內核定賠償金額”的規定,應認雙方對“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有關法律法規”約定的真實意思為保險事故發生時實施的法律法規。即使雙方當事人對此約定理解不一,那么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規定,對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應當作出有利于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理解的,應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條款的一方的解釋,對本案所涉保險條款中“國家現行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的膠在法律法規”為保險事故發生時實施的法律法規,故上訴人應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賠償標準,在保險合同約定的賠償限額內承擔保險責任。上訴人提出本案應適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的計算方法進行理賠的主張,無事實和法律依據,本字不予采納;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未履行寧波市鄞州區人民法院(2005)甬鄞民一初字第108號民事判決,被上訴人的實際賠償額尚未確定,故要求上訴人賠付該民事判決確定的賠償額依據不足的上訴理由,因該賠償額款,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實際全部賠付后才能向上訴人理賠,無法律依據,本院亦不予采納。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實體判決正確,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篇3
浙江志遠大律師事務所接受李鳳的委托,指派程世峰律師處理貴司與其之間的工程款糾紛事宜,根據調查確認事實,結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特致函如下:
一、本案事實
我委托人李鳳負責的施工隊按照貴司嘉興中科院項目部相關工作人員的要求,于2006年11月至2007年6月對中國科學院嘉興應用技術研究與轉換中心一期幕墻工程1號樓幕墻進行施工活動,共完成114691.95元的工程量和27295元簽工工作,經過貴司提出處理意見和最終確認,貴司總共應付我委托人李鳳工程款金額為141900元。工程完工以后,雖然我委托人多次到嘉興懇請支付工程款,但貴司拖延支付。在我委托人無數次催討的情況下,2008年2月3日,貴司才勉強支付我委托人3萬元工程款,其余款項仍然不愿支付。這種情況下,我委托人于2008年2月3日向貴司遞交催款函,要求貴司必須至遲2008年2月4日前全額支付剩余工程款,該函由貴司財務簽收。貴司簽收催款函后,我委托人又多次以電話等方式聯系貴司負責人王緒杰,但要么是電話關機,要么是無人接聽,直到現在貴司仍然在躲避支付我委托人工程款。
二、法律依據
1、根據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
根據合同法第三十六條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
依據法律規定,貴司與李鳳的合同關系成立,雙方應嚴格遵守相互關于工程方面的約定和相關法律規定。
2、根據合同法第六十條規定“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全面履行自己的義務。當事人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根據合同的性質、目的和交易習慣履行通知、協助、保密等義務。”
依據法律規定,貴司應按時支付李鳳工程款,貴司沒有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工程款,沒有全面履行自己的合同義務,屬嚴重的違約行為。
3、 根據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承擔繼續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
依據法律規定,貴司應該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李鳳可以要求貴司賠償損失。貴司應當在2007年6月20日工程完工時支付全部工程款,李鳳可以要求貴司支付拖延付款期間的滯納金和到嘉興索要工程款的交通費等費用。
三、律師意見
根據本案委托人李鳳提供的案件事實,結合相關法律規定。本律師認為,不管因為什么原因,作為合同的一方當事人,貴司的行為明顯違約。李鳳完全有權利通過法律途徑要求貴司支付應付的工程款和要求賠償損失。貴司應當及時支付,否則除承擔工程款外,還需要承擔近萬元的其他費用,如滯納金、交通費以及貴司聘請法律服務人員的費用等等。
四、鄭重提醒
根據委托人的要求,本律師鄭重提示:自收到本律師函之日起3日內,向委托人李鳳支付其應得的工程款。如未在本函規定的期限內交付上述合同款項,李鳳將委托本所向貴司提起法律訴訟,追究貴司的違約責任。望貴司在收到本函后及時給付,付款事宜可以與李鳳或本律師聯系。
特此函告
篇4
【摘要】自首作為我國刑法確立的一項重要刑罰制度,是具有其獨特的積極意義的。但是實踐中,交通肇事罪基本犯是否適用自首一直存在較大的理論爭議,本文分析并闡述司法實踐中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自首及自首的認定的問題的相關思考,以期在理論上有所突破與創新,為交通肇事罪的司法實踐和交通肇事罪立法的完善貢獻綿薄之力。
【關鍵詞】交通肇事罪;自首;逃逸
一、我國交通肇事罪立法情況及特征
(一)交通肇事罪相關立法規定
1979年刑法第113條對交通肇事罪做了具體規定,1997年刑法對交通肇事罪作出了重大修改。1997年刑法使得刑法理論界對交通肇事罪的關注更加廣泛,對交通肇事罪的研究也成樾碌娜鵲恪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對交通肇事罪的具體適用問題作出了統一規定。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對交通事故的認定及處理辦法等問題作出了更加詳細的規定,為交通肇事中的罪與非罪的判斷提供了操作性更強的法律依據。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l)》第二十二條規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后增加一條,使醉酒駕駛和飄車兩項危險行為正式入罪。
(二)我國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特征
1.規定主觀過失,排除故意犯罪
從我國關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規定上可以清晰的看出,其主觀方面必須是過失,從我國對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沿革、設立背景就一早已劃清過失與故意、此罪與彼罪的界限,將其限定為過失類犯罪,而排除了故意犯罪。因此,交通肇事罪仍然是個過失犯罪。
2.規定肇事后果,排除危險預期
在我國,交通肇事罪屬結果犯,即只有達到法律規定的肇事后果才能構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致人重傷、死亡及其對事故所負責任,造成財產損失的額度都是罪與非罪的界限。
3.列舉肇事結果,劃分量刑檔次
我國對因交通肇事所造成死亡、重傷、財產損失的結果是作為定罪的依據,既不規制前置危險,也不另立后果加重的新罪名,即在法律所規定列舉的幾項后果范圍內,劃分三個量刑檔次,均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4.涵蓋逃逸加重,規制不救助行為
根據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都作為更重一檔法定邢的情節。這里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對逃逸行為的懲治,在某種程度上激勵了肇事者履行救助被害人的義務。
二、交通肇事罪自首成立與否的理論支點
絕大多數學者是承認過失犯罪是存在自首的,完全否定交通肇事罪存在自首的觀點基本已經很少有人提及,但是在哪種情況下該認定自首,哪些情況下不該認定自首卻存在以下兩種爭論。
(一)否定論的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自首制度對分則的適用具有普遍性。第一,肇事行為人待在原地等候處理并非真正悔過。第二,通常說來,適用自首制度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節約辦案成本,但交通肇事罪中認定自首卻未必能達到這樣的效果。第三,認定自首就會造成交通肇事罪的斷檔,會違背刑法針對不同犯罪設立不同法定刑的立法原意。第四,行為人肇事后等候處理和報警等行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要求必須履行的法律義務,排除自首的適用。
(二)肯定論的觀點
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我國是比較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當屬成文法。交通肇事罪作為一個個罪,不能夠排除在自首制度適用的范圍之外。
首先,當事人履行法律規定的行政義務不能排除刑法中自首的適用。行政法上規定的義務與刑法自首制度相符,可以這樣理解:二者在法律規范要求上,具有殊途同歸的立法旨趣,但是不能認為前者是法定義務就否定后者的適用。
第二,交通肇事罪通常情況下具有一定的公開性,但這不能成為否定交通肇事罪中存在自首的理由。
第三行為人報案的具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無論是委托他人報警還是自己親自報警,無論是自動去公安投案還是經他人勸說投案,無論是出于害怕報案還是真正悔過報案等等,都不應當成為行為人不能成立自首的理由。
三、交通肇事罪自首的認定
(一)委托他人報警是否屬于自首
在確定為自首后更應該明確的是,在認定成立自首之后,最后的案件判定、自首從寬的幅度還要綜合考慮不同的犯罪情節、不同的犯罪事實以及不同的犯罪嫌疑人的認罪態度和悔罪表現。自首不是法定應當從寬的情節,并不是所有的自首都全部從寬,這就意味著,存在自首情節的犯罪是否從寬以及如何從寬都是要根據具體每個案件的情況進行認真分析,嚴謹辦案以盡量避免前面所述的擔憂。
(二)明知他人報警,在原地等候處理是否成立自首
對于行為人明知對方報警,自己沒有報警但是待在原地等候警察來處理的,是否成立自首,在實際審理過程中,也存在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有的認為應當認定成立自首,原因是此類情形在其他普通刑事案件中一般均認定為自首。
(三)逃逸后主動投案是否成立自首
行為人肇事后逃逸,之后無論出于何種緣由只要其自動投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就應認定自首。但是,如果行為人投案后又選擇逃跑,在這種情形下就不能再認定自首了,這種情形與特別自首不同。另外,如果行為人肇事逃逸后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在供述完自己的罪行之后又翻供的,基于法律規定,也應當認定自首的成立。
參考文獻:
[1]趙秉志.《刑法修正案(八)》理解與適用[M].法制出版社,2011
[2]張明楷.論交通肇事罪的自首[J].清華法學,2010
[3]邊學文.論自首制度在司法適用中的若干疑難問題[J].法學雜志,2010(11)
[4]吳云.交通肇事罪認定若干問題研究[J].政治與法律,2009(8)
篇5
論文關鍵詞 職務侵權 替代責任 雇員責任 追償權
一、案情介紹
汽車服務站員工鄭某駕駛維修完畢的車輛送歸車主馮某的途中,與騎行電動自行車的錢某發生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鄭某負事故主要責任,錢某負事故次要責任。錢某訴請要求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超出的部分由鄭某和馮某承擔80%的賠償責任,并由汽車服務站承擔連帶責任。
一審法院認為馮某對錢某受傷并無過錯。鄭某系汽車服務站雇員,其主張將修理完畢的車輛送還馮某的行為應屬職務行為,汽車服務站對此不予認可,認為是鄭某私自將馮某的車輛開出汽車服務站并導致交通事故,然汽車服務站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故不予采信。鄭某的送車行為系與其工作內容相關的行為,可以認定為職務行為。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用人單位承擔侵權責任。故判決原告錢某所受的合理損失,應由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責任限額內按照實際損失賠償,超出部分,由汽車服務站賠償80%。
汽車服務站對一審判決不服,上訴稱,汽車服務站對修理完畢的汽車無上門送車的義務,鄭某是在汽車服務站未授權、而車主馮某授意的情況下,擅自送回車輛的,故鄭某與馮某對事故發生均存有過錯,要求二審改判該兩人承擔賠償責任,汽車服務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故要求撤銷原判,依法改判。
二審法院認為將修理完畢的車輛送回車主處不啻為汽車修理行業的一項服務內容,因汽車服務站對其主張未提供相應的依據,故本院認定鄭某的行為系職務行為。雇員在履行職務行為過程中造成交通事故,經交警部門認定負事故主要責任,應認定其具有重大過失,依法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汽車服務站上訴要求鄭某承擔賠償責任,有事實與法律依據,予以支持。汽車服務站上訴要求馮某亦承擔賠償責任,無事實依據,不予支持。原審法院未認定鄭某具有重大過失,存有不妥之處,予以糾正。
二、司法實踐情況
本案所涉職務侵權在道交案中很常見,通常的情況是駕駛員所在單位認可駕駛員系在履行職務行為,出庭表示單位愿意承擔事故在交強險外的賠償責任,鑒于此原告通常會主動申請撤銷對駕駛員的訴請。員工在履行職務行為過程中致他人損害,由用人單位承擔賠償責任,這一原則在當今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了普遍的共識,尤其是在道交案件中,用人單位考慮到有保險,通常都比較自覺地出面處理賠償事宜,至于單位賠償后是否追償是單位與員工之間的內部協議和內部管理問題。目前單位在履行道交賠償后向員工追償案件尚屬罕見。
當然也會出現一些單位認為其員工在履行職務的過程中,是員工自己的原因致他人損害,由用人單位賠償大額的費用很冤枉,就如本案例的情況。在另一起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案件中,員工作為駕駛員,逆向行駛致人受傷,并被交警認定為全責,用人單位認為這種情況應是員工的過錯,主張自己最多與員工一起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該案判決由用人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用人單位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二審維持原判。由此可見,在司法實務中,對職務侵權案件的法律適用不一致,如適用《民法通則》關于職務侵權規定,則是由企業法人作為用工單位承擔替代責任。如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則不只是雇主承擔替代責任,若雇員有過錯或重大過失,應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如適用《侵權責任法》,則僅明確規定了用人單位的替代責任,未規定雇員擔責情形。案例中一審和二審的不同判決,恰是因為適用法律不同。
三、現有法律規定的偏失及法律適用問題
(一)在雇員責任和雇主追償權問題上,法律如何適用尚存爭議
現行法律未明確雇員責任,這造成一種普遍的社會認識是凡是在工作中致他人受傷,均由單位承擔賠償責任,雇員無須對外擔責。正是如此,在司法實踐中才會有絕大多數的用人單位都會乖乖的認可雇員的職務行為,主動承擔責任,且不追究雇員責任。
現有法律也未明確雇主的追償權。雖然前文已述,侵權責任法并不否定此權,但未明確寫在條文中,一般民眾并不了解,故造成一種假象是雇主在承擔了責任后,不能再找雇員追償。由此形成現在普遍的現象是:用人單位對于員工因職務致人損害的,只能通過內部機制進行懲處,或罰款或辭退等,但免不了對外承擔賠償責任。而員工則以為自己在工作中致他人損害,無須承擔賠償責任,也就不會盡到足夠的注意和風險防范。尤其在一些流動性較強的行業中,如運輸行業,駕駛員多是受雇于人,造成交通事故的,由雇主承擔賠償責任,駕駛員只要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以至于上升到刑事責任的地步,都可以甩甩手走人,另尋他處謀職,罰款或辭退對他們并不存在約束力。這形成了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致使職務侵權行為多發。
在本案例中,一審法院適用了《侵權責任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作出判決,對雇員是否有責任再所不論,由雇主承擔責任。而二審法院則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的規定,雇員有過錯或者重大過失的,應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那么,在涉及到雇員有過錯或者重大過失的情況下,該如何適用現有的法律規定?
追溯原因,這是侵權責任法制定遺留給司法實踐的難題。在侵權責任法草案審議報告中指出,草案三次審議稿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規定了用人單位工作人員因工作和個人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產生的責任。一些常委會組成人員建議增加規定用人單位和接受勞務一方的個人對他人賠償后的追償權。法律委員會經同有關部門反復研究認為,在什么情況下可以追償,情況比較復雜。根據不同行業、不同工種和不同勞動安全條件,其追償條件應有所不同。哪些因過錯、哪些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可以追償,本法難以作出一般規定。用人單位與其工作人員之間以及因個人勞務對追償問題發生爭議的,宜由人民法院在審判實踐中根據具體情況處理。由此可見,立法者并不否定追償權,但在什么情況下追償,立法者未給出一個統一標準,故留待司法實踐中探索。
由此可見,在侵權責任法出臺后,雖終結了用人單位主體的混亂,卻又開始了雇員責任及雇主的追償權問題的混亂。
(二)如何認定雇員的過錯
雖然侵權責任法在關于職務侵權的條文中未予明確規定,但是在《侵權責任法》第六條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或可依此過錯責任原則主張雇員的過錯責任。但是此處的“過錯”并不同于《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九條之“過錯或重大過失”。根據過錯原則的能說,過錯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形態,侵權行為人所應負的責任與其過錯程度相一致。那么在職務侵權中,是否應提高對雇員個人擔責的過錯程度要求呢?
關于這一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態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理解與適用》對用人單位是否享有追償權的問題做了如下說明:“盡管本條沒有明確規定用人單位的追償權,但在審判實踐中如果用人單位能夠舉證證明侵權行為是由于其工作人員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且該行為超出了法律賦予的職權或單位的授權范圍,用人單位可以向具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工作人員進行追償……審判實踐中,只有在工作人員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且該行為超出了法律賦予的職權或單位的授權范圍,造成侵權時,用人單位才享有向該工作人員追償的權利。”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最高人民法院不只要求雇員的主觀是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還要求其行為超出了法律賦予的職權或單位的授權范圍。相比較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對于用人單位追償權的態度雖持肯定但更加嚴格。如依此態度來評斷本案例,則不僅要認定駕駛員鄭某的行為系重大過失,還應證明駕駛員鄭某雖表面上履行的是職務行為,其行為外觀上與雇主利益相關聯或與工作相關聯,但實際上已經超了工作的授權范圍。而本案在二審中并未有體現,僅是在確認了履行職務行為的前提下,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九條之規定作出判決。
對雇員過錯的認定確難以把握。以道交案件為例,肇事方必是過失侵權,如何認定為重大過失呢?是否被交警認定為主要責任或全責的,即為重大過失呢?如依此一概而論,那么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機動車駕駛員基本上均可被認定為有重大過失。
四、對職務侵權法律適用的建議
(一)關于雇員的責任
借鑒英美法系及大陸法系主要國家的法律規定及判例,雇員在執行工作中致人損害,并不能免責,應就其過錯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國內也有些觀點認為應確定雇員的責任。①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筆者贊同本案例中二審法院的觀點,適用《人身損害賠償解釋》第九條之規定,從寬考察雇員的責任。這樣可以約束雇員在執行工作任務過程中的行為,盡到安全保障和注意義務,以謹慎的態度避免侵權行為的發生,還可減少雇主在經營活動中的風險和負擔。
(二)關于被告的問題
受害人可以只起訴雇主,也可以一起起訴雇員和雇主,甚至可以只起訴雇員。這充分體現受害人的訴訟權利,其可以考慮到對方的償付能力以及個人利害關系等,自行選擇賠付主體。